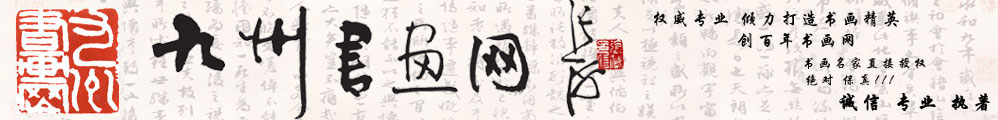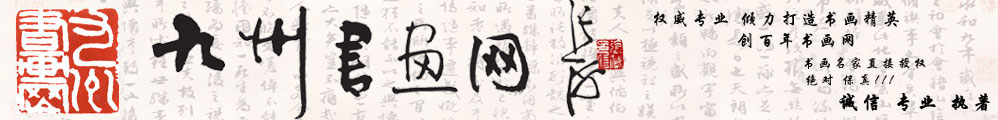红色台风
那是1969年中秋过后的一个晚上,月亮还未升起,天空尚有稀疏的星星在闪烁,一颗流星在高大的梨树上空短短地划过。吴稚农正在后院子里的梅树下吹着洞萧,他刚学会吹《妆台秋思》,颇为自得,正想站起来走动一下,忽见围墙上闪出一个黑影,同时轻轻地叫了一声:
“小龙。”
“啥人。”
那人立即跃下园中。吴稚农一看,是石门镇上有名的窃贼癞痢阿星。
“啊哟,阿星,你找错了,我小龙家里东西被抄家抄得差不多啦。”
“小龙,我不是来偷东西的。”
“那你干吗?”
他伸出手来:“你看了就明白。”
在星光下仔细辩认,有两行字:“小龙,我肚子饿,叫他带点糕饼来,洪浩。”
吴稚农一看便知沈洪浩的笔触,沈是与张星逸、叶瑜荪等朋友。
阿星说:“我与沈洪浩关一起,你看家里有啥拿啥。”
“阿星你既然已逃了出来,你还要再回去?你真够义气!我佩服。好,我去拿。”
吴稚农叫他进屋,拉开电灯,开橱门拿饭菜,先让他饱餐一顿,自己出门到隔壁小店买了两筒月饼。
阿星说声:“谢谢。”便拿了月饼,出后门飞速回去。原来他们关在东高桥堍的药材加工厂。沈洪浩是修理家用电器的,他的罪名是偷听敌台。
过了两天,差不多时候,癞痢阿星又翻墙进来,说还要吃一顿。摊开手,沈洪浩写着:“再来两筒,感恩。”
阿星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只手表,一看是英纳格的,说道:“小龙,送给你。”
“我不能拿!你想害我。”吴稚农一手推开。
“那就放在你这里,待我出来后我来取。”
“那更不能。你拿出去,找个地方放好。不过我劝你,最好是还给人家,那丢表的人正急得要命哩。你听我大哥一句话,今后正正派派干个工作,还能成家立业。”
“小龙阿哥,我听你。”说话倒很有诚意。
吴稚农说:“你饭吃饱,这里还有点冬瓜咸肉,你都吃了吧。这手表赶紧去还。你真够厉害,在这种情况下,还能拿到东西。”阿星说:“我是在药材厂宿舍用一根铅丝伸进窗里勾出来的。”阿星又一本正经地说,“啊哟,我是想感谢你。”
“谢谢了,你的心我领了,我告诉你,做这种事肯定要有报应的,你到此为止吧。你还是再用铅丝送进去”。
又过了两天,一个淡云微月之夜,速忽又下起小雨。吴稚农把书房的窗户关好,把白天画的速写整理一下,磨了一点墨在宣纸上试画起来,他一张接一张地画,并用图钉钉在墙上,自我欣赏着,忽然觉得后门有响动。
“笃笃、笃笃……”原来有人敲门。
吴稚农便急急跑到园子的后门,贴着门轻轻说:“谁。”
“是我云林,快开门。”
王云林是个体牙科医生,吴稚农的牙齿不太好,常常去他那里补牙。这次他也是偷听敌台而被关起来隔离审查的。
吴稚农一想,真行啊,都到我这里来要吃的。好啊,祖母说帮人家要像还债一样心甘情愿。
吴稚农开门便说:“快到里边吃饭。”
“不吃,你赶紧拿点吃的,给我带回去,我怕时间长了被人发现,就麻烦了。”
吴稚农即到楼梯下的石灰甏里把所有的糕点打了一个包,叫他拿走。
王云林拿着东西,声泪俱下地说:“小龙啊,我罪业重,看来要坐牢判刑。”
“我不信,有这么重吗?”
“啊哟我一直在听美国之音,自由中国之声,连蒋介石的声音都听到过。”
“嘿,你算什么?一个装牙齿的不可能跟蒋介石有什么关系?”
“你不懂,总之,我坐牢无疑。碰到我老婆芳芳,你叫她不要离婚,等我刑满回来。”
“好,好,你快回去。”
吴稚农又回到书房,真的没劲画画,想来想去想不通,收听收音机要判刑,真是匪夷所思。
吴稚农躺下来睡了一回,忽然外面有敲门声,敲得很急,吴顺发去开了,父亲叫吴稚农快下来。他一看是镇革委会的人,还有工纠队的,其中一人道:“刚才王云林到你家来过?”
“是的。”
“你跟我们到工纠队去一趟。”
原来王云林一回去,就被守在那里的工纠队碰上,一严厉盘问就交待出来。再说沈洪浩与癞痢阿星、鲍瞎子、杨鬼头三个小偷关在一起,月饼拿去后,他们之间分不均匀,便打了起来,杨鬼头咬掉了鲍瞎子半只耳朵。工纠队员悄悄在听他们为何吵闹,得知是为了月饼,开门一查,问道月饼何处得来,起先都不说,后来工纠队用了蛛蜘吊刑罚,才说出来。
吴稚农来到药材加工厂,在一个打包车间里,有六七个工纠队员,有人喊他跪下。吴稚农不跪,便过来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地,用麻绳把他反绑起来。在捆绑时,吴稚农一边犟一边叫:“你们当我是什么,我又没罪,你们想搞逼供吗?”
“你没罪,我们不会抓你,你跟反革分子沆瀣一气!”此人狠狠地拍了一记桌子:“你老实交待,你跟沈洪浩、王云林他们是上下级关系,还是什么?”
“我们又不是什么集团,怎么是上下级呢?”
“你还不承认?把他吊起来。”
其中一个把一根长长的麻绳抛过上面的横梁,用力一拉,吴稚农反绑的双臂即刻拎起,后来又上去一个,再一拉,他人就脱空吊起了。开始凭着臂力屏了下,觉得还行,后来臂上的血液由于阻流而由疼痛转为麻木,体力渐渐不支,头上黄豆大的汗珠出来了,想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,再下去可能要把臂扭伤,便说:“好,我交待。”
“放下。”
放下后,他们把绳子解开,并为吴稚农的双臂按摩了一下。吴稚农说要喝水,要纸笔,要小便,他们都依了。后来吴稚农说:“我累了,要睡一下,明天肯定交待。”
结果工纠队们把他关在打包机的模子里,他们把电源拔了。里面很坚固,你再大的本事也逃不出来。吴稚农有点累乏了,弓着腰,缩紧身子慢慢地睡着了。
次日一早,另来几人把他带到一间小房子里关起来,端过来一碗粥、一条酱瓜,其中一人有点熟,对他说:“小龙,你好好吃,一天规定七两米,不够吃也得吃。”
吴稚农在写交待书时,还是写清事实,不是集团,不是上下级,沈洪浩、王云林他们即使有多大的罪,他们肚子饿,要东西吃,给他们也是正常,人总该有点人性。
工纠队看了很不满意,说:“对待反革命有什么人性不人性的。革命是用鲜血换来的,你知道吗?他们反革命,就是糟蹋鲜血,糟蹋鲜血的人,是没有人性的,你这个人性是白用的。我们已去你大队调查过了,你早已是现行反革命了。你只有老老实实地作深刻的交待。否则,你就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”
“砰”一下把门关上走了。
就在这天夜里,门外有人在说:“十二点快到了。”接着就开门,吴稚农瞌睡蒙瞳跟着他们出去,说要转移地方,一共有十多个人。
吴稚农恍惚地来到一个地方,叫他们一人一格住下,一看原来是烘茧的灶。下面铺着一条狭席。
“行啊。”吴稚农轻轻哼了声便躺下身睡了。
“咯笃”一声,灶门闩上了。一片漆黑。
这里是第一次批斗他的南皋桥茧站。
“嗡嗡嗡”有一只蚊子,后来发觉不止一只。他有点烦,想等候蚊子叮着后把它拍死。忽然听到里边笃底的屋子里有哭声传来,是一个成年男子的哭声,很低沉,还夹着鞭子抽打的声音,这是个不祥之声。蚊子叮在脸上了,“啪”一声,打死了一只。算了,另一只蚊子不打了。次日早上睡觉醒来是被开茧灶门惊醒的。一看是镇委书记老孙,他叫了一声:“吴稚农,吃早粥,我放在门口了,”这书记是一脸晦气,靠边站了。
在吃晚饭时,在白米饭上有一筷菜。现在吴稚农已有经验了,这菜要配合好饭的总量来吃下去。吃到最后一口饭时,还有一条菜叶来拌下去,想不到这条菜又甜又香,而且回味无穷,简直无法形容它的美感。
老孙送来一只痰盂、一刀草纸,还有一把破蒲扇。吴稚农把蚊子赶了一下,把里面的那只二十五瓦光电灯关掉,就打算睡了。
他还未入睡时,门外过道里有几个人的脚步声,一直走到他的门口,门开了。
“吴稚农,快出来,出来!”
吴稚农跟他们来到了里边最笃底的屋子。一看这里的门、窗都挂上了厚厚的棉被,就知是为了隔音,灯很亮,亮得刺眼。他站着,对面坐着三个人,中间一人像是在记录,他背后有四个人手中拿着鞭子绳子的。吴稚农心想:“今天肯定要吃皮肉之苦了。但你们搞错了,我身上没什么花头,我是个普通的老百姓。”
审讯开始了。
你叫什么名字、年龄、性别、民族。吴稚农一一回答。
“你的《燕山夜话》怎么来的?”
“崇福新华书店买的。”
“那本《分阴集》呢?”
“也是崇福买的。”
“不对,是新市买的,书上有章。”
“噢,我记错了,是新市。”
“你到新市干吗?”
“我去画人像。”
“你到处串联,你的上级在哪里?”
“我一个画像的,做油漆的,要上级干吗?”
“你要反党,你仇恨无产阶级革命。”
“啊哟,我做做油漆、拍拍照,生活还可以,干嘛要反党呢?”
“对了,有人见你爬在屋顶上拍全镇照片,告诉你,你这是犯法的,这些照片在军事上有用的……是谁叫你拍的?”
“我自己想拍。”
“你又赔工夫又花钱,你什么用意?”
“我觉得这个镇很美丽,水乡味很浓,如果一旦有什么拆旧建新的话,这些照片也是一份历史资料。”
“你有这么好吗?……老实点,想不到你真会说话……你快交待你上级是谁?”
“我实在没有,如果你一定要我说一个上级的话,那我的上级——是你!”
“啪、啪”两记用三角带做成的鞭子,落在吴稚农的屁股上,第二记他用左手一挡,手腕上即刻出现了一条肿起的肉筋。接着又被抽了一鞭。
“吴稚农,你自讨苦吃。”那人显出一副很惋惜别人的样子,而且好像很真诚。
吴稚农心想,这比电影里演的还要精彩。
突然有人在吴稚农的膝弯处猛然一踢,他没防备经不住跪了下来,接着马上有一根木棍压在他的腿肚上,一面一人站在棍上,吴稚农感到有一种钻心透骨的疼痛,遂即倒下身子,双手发起抖来,口吐白沫。
那些人一看以为他昏过去了,便提起一桶冷水当头隔脑一泼。他还是没有反应,便把他暂时抬到另一间小屋内。
其实工纠队的人想立功,想逼出一个反动集团来上报。他们对准了吴稚农开刀,因为此人社会关系复杂,又是能文能武的多面手。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,再说他是四类分子子女,又有前科“现行反革命”,即使把他搞垮了,也是无可翻天的事。
吴稚农已经看出了他们的意向,这一可怕的意向,他必须作出应对。他没有昏去,脑子很清醒,唯一可试一下的办法就是装疯,但很危险,很累的……又一想,如果不装疯,那就更危险。
吴稚农听到有脚步声,便当机立断:“从现在起,我是个疯子。”于是嗯嗯呀呀地哼起二胡曲来……但脚步声没有过来,再一想哼哼曲子算不了疯了,疯子必须大小便失禁,吴稚农忽然想要大便,但穿着裤子躺着随你怎么涨也涨不出来,小便也同样,他只好站立一下再蹲下去,蹬着、涨着,果然出恭了,小便也来了。但是臭气充满整个小屋子。实在不好受,此刻他又想起了西藏佛教徒消业障的过程……对,这是在消业障,今后我肯定辉煌。吴稚农把自己的心态总算稳住了。
外面有人在说:“是什么臭?”
“在小屋里,快拿钥匙来。”
门开了,电灯亮了,吴稚农在向他们傻笑。
“不好了,这只毒棺材真的疯了。”
天快亮了,他们叫来一个“坏分子”给吴稚农擦屁股,同时叫人到他家把衣裤拿来。
因为大便被坐着躺着后沾得一塌糊涂,来了四个四类分子,把吴稚农抬到井边,剥光了衣裳冲洗起来。
家里的衣裤换上后,他们用铁链把吴稚农的手脚都锁起来,边上有几个工纠队员在说:“这只毒棺材有武功的,真的发起来,我们这些人都要不过他的。”
“把他的头发理一下。”
“理发干吗?”
“等会小轮船来了,去乌镇精神病医院。”两个工纠队员在说。
一会儿他们拿来了几个菜包子,吴稚农狼吞虎咽吃了两只,第三只他只吃了一半,便用力一喷,那喂食的人给喷了脸,引来大家一阵好笑,但吴稚农没有笑,不能笑啊,一笑就完了。他只要想起他们可怕的意图,他就笑不出了。
后来过来个有点历史问题的剃头司务说:“吴稚农,乖点,我给你理发。”
吴稚农心想最好理到一半不理了,就像个疯子了。
当理到一半时,吴稚农双眼凶狠地盯着那个理发师,那人立刻停止了理发,耷拉着脸哀求他:“吴稚农,你不要这样看我,我怕,我吓不起……你不能咬我呀!”
“你怎么停着不理发,快点。”一工纠队员说。
“你看,我不敢靠近他。”那理发师哭丧着脸说。
“啊唷,我来我来,小龙,我到你家去过,你给过我画,我们是好朋友了,来,我给你剃。”一个镇革委干部过来说。
此人是人武部长张济昌,人不错,吴稚农向他点点头。张部长会剃头,便拿起轧剪轧起来,前面轧了一下又转到后面。吴稚农坐在一只半高凳上,又反绑着手,张部长穿着一条西装短裤,与他靠得很近,突然吴稚农做出一个非近人情的动作,伸出手指,迅速得如同抓泥鳅一样地把张部长裤裆里的东西揪住不放。
“喔唷,小龙,你放,你放,你要不得。”张部长尴尬地惊叫。
“怎么啦?”
“什么事?”
“好啊,呱呱叫。”大家仰前扑后地笑,吴稚农没有笑,张着嘴,注视着一个方向,那些工纠队员举起棍子吓唬他也没用,后来张部长丢掉轧剪用双手把吴稚农的一只手扳开。吴稚农心想这是第一场考验。
“小轮船来了。”
“不剃了,就这样算了。”
到了乌镇的精神病医院,患者很多,那主治医生陆医师,吴稚农认得,前年母亲发病时,陪同母亲来过,但陆医师已不认识他了。
吴稚农想要小便了,不妨披露一下工纠队打自己的罪行,于是奔到门诊室对面的天井里掀下裤子,拉起尿来。立刻引起众人哗然惊叫:“屁股上打得利害咧。”“这世道!”
工纠队人员赶紧去把裤子拉上。
当要轮到吴稚农诊治时,那头头跟陆医师说:“看看此人是真疯还是假疯。”
陆医师说声晓得,便吩咐让病人躺下来休息一会,十分钟后再观察。吴稚农一听,不好,十分钟后心跳肯定正常,遂即开始用劲,当然躺着的人只有头脚着力方可加速心跳。
十分钟很快过去了,陆医师用听筒在他胸口一听,问道:“是十分钟吗?”
“十二分了。”
“有点重。”陆医师轻轻对他们说。
接着陆医师又搔了一下他的脚底,没有反应。再抬起他的膝,吴稚农还是屏着,敲了一下稍微有点反应。
最后陆医师查看瞳孔,吴稚农就把眼珠一直往上挺,医师用手去扳眼皮,越扳越向上挺,根本无法诊断。
看病的人很多,排着队。
陆医师坐下来,在病历卡上写了“轻躁狂精分症”。
“精分症是什么病?”那头头问。
“就是精神分裂症,真毒头,不假,配了药片,按时给他服用。现在要给他打一针氯丙晴,如果他是真疯,可能要半个小时睡着。假疯的话,五分钟也不需要。”陆医师边说边在他的屁股上打针,吴稚农就不断地歌唱、哼曲子,坚持了半小时。
吴稚农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了,终于战胜了,凭着强硬的意志力,终于转危为安了。
回到石门茧站,他们对吴稚农改变了态度。首先给他睡了一张有蚊帐的床,饭可以吃饱了,家里人可以来看他,可以带东西给他吃。
摆在面前的难题是吃药了。好在这些药片很小,又是孙书记负责喂药,老孙自身难保,也没多大注意。
“吴稚农,吃药了,把手伸出来,”老孙有气无力地说,吴稚农接了药,手一握,先把药卡在手指之间,再伸手仰头作吃药状,遂即用开水一过,吞了一下,过了一回,他去厕所把药片搓成粉沫,趁没人见时扔了。
头两天,吴稚农断断续续地哼着《二泉映月》或者刘天华的《病中吟》。
后来,便慢慢地正常起来,好像是药物治疗起了作用。
十月国庆过后,茧站里快要开始收秋茧了。工纠队要抓紧审讯,赶快结束这次红色台风。
就在这天晚上吴稚农见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:
一个联总造反派头头,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青字,所以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青肚皮,这次他在审讯一个曾参加过三青团的嘉兴人,问他会见蒋经国的事,那人不开口。便命令一个有历史问题的叫孙有良的人用扁担打他。起先孙有良只是做样子地打了几下。青肚皮笑着说:“孙有良,看来要我教你打,把扁担给我。”
孙有良把扁担给了他。
“你趴下。”青肚皮用手指下地上,“快,你识相一点。”孙有良立即趴在地下。
青肚皮轮起扁担,用扁担侧面狠狠地在孙有良的屁股上一记。
“啊唷!”孙有良大叫。
“你会了吗?不会我再教你。”
“会了,会了。”孙有良带哭含笑地说。
“好,那就看你的了。”青肚皮说着,把扁担递给他。
孙有良定了定神,就举起扁担平打,还是下不了重力,只是比前重了点。
那时青肚皮干咳了几声说:“孙有良,看来你还没学会,把扁担拿来,我再来教你。”
“会了,会了,我会了呀!”孙有良哭了。
“会了,你就做出成绩来。”
孙有良真的用劲打了“啪”一声,手脚都被工纠队员按住的三青团员 “哇”地一声叫着。
“不对,要侧起扁担。”青肚皮凶狠地说:“连着打。”
“呼呼,呼呼,”“往上打。”青肚皮指着手势说。孙有良也已泼出了灵魂,失去了理智,在腰部狠打一记,三青团员已不叫不动了。
一个工纠队员忙说:“不能打了。”
青肚皮嘴上说着:“他装死了吧。”赶紧扳过那人的脸,果然眼睛翻白停止了呼吸。
“啊呀,闯祸啦!”孙有良发着抖喊着。
“滚,你不许多说,说出去就跟他一样。”青肚皮叫孙有良回茧灶。
过了一回,青肚皮叫来了一个“不法资本家”毛乐庐,命令他用一根麻绳套在三青团员的脖子上,背着尸体来回走。吴稚农闭上眼睛不看了。
青肚皮想以指其为“上吊自杀”来传呼他家人领取尸体。当然其家人不肯轻了其事,遂请法医检验,结果定为敲打致死。
青肚皮逮捕入狱,判刑十二年。
石门工纠治安大队释放吴稚农时,“将”了他一“军”。
“吴稚农,我们同你去乌镇看病,你知道吗?”那头头阴阳怪气地问他。
“知道。”
“专门为你借来了小轮船,又为你垫付医药费,你总得付呢,总共要三十六元钱。”
吴稚农低着头不吭声,在想:“你们把我逼成了病,我不跟你们算账了,你们却要向我收钱?但我不能这么想,那是我的业障,必须要付的。”
“你怎么不说话?”
“我没钱,这钱应该付,欠一下行吗?”
“那倒可以……什么时候还呢?”
“等我去做漆匠,赚了钱,再还。”
“行啊。……对了,我们镇革委的门窗该油漆一遍。你去找程文书联系,好吗?”
“好。”吴稚农当然高兴。
“你去整理东西,今天就出去,回家休息几天,再去油漆。”
过了几天,吴稚农去油漆了,算了一下价格,最多五十元,便喊了七十元,准备他们还价,但他们不还价,只说了一句:“这只毒棺材,毒进勿毒出。”
吴稚农医药费没有付,但工纠队没向他要。
后来吴稚农碰到那头头,主动提起那医药费的钱说道:“因为家中困难,是否能再欠一下。”
“算了吧,我们看你人不错,这点小钱,我们公家报了。”
吴稚农一想,业障消了。
此事,称之为“红色台风”,真的像暴风骤雨似地过去了。
吴稚农亦以消业障视之,逢人只是傻笑,许多人以为这只毒棺材真的疯了。他的油漆双活不多了,拍照也不允许拍,命他把全镇照片送到工纠队销毁。吴稚农拿了些照片去,但底片没有交,他们也不说要底片,他们是真的不懂,还是假的不懂,就不得而知了。
回小队劳动,吴稚农也是不情不愿,自留地也不好好做,他知道在自留地中,也得不了多少的经济收入。只有那些老实巴巴的人,在没有任何经济来路的情况下,拼命啃挖。
在这段时日内,吴稚农在命运的重压下心灰意冷,心绪一蹶不振,觉得这社会不公平,农民太苦了、太愚昧了。他想写小说,但又静不下心。他听说桐乡二中的一位姓朱的教师,写了十万字的中篇小说《古运河畔》,反映三年自然灾害中的农村现实,被判刑十年。吴稚农想,自己犯不着去冒这个险,后来,实在憋不住,还是想写,就用了童话体裁写了一篇《麻雀的遭遇》,很巧妙地描述了一只小麻雀的成长过程,碰见了许多所谓益鸟也在干坏事,它被列为四害之一麻雀,却在干着一些有益于农作物的好事。当它要受到人们的驱赶与捕杀时,带领伙伴们逃到了远离尘世的深山,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吴稚农把那篇《麻雀的遭遇》寄到了《少年文艺》杂志社,结果被退了回来。编辑写了几句话:“此篇内容不真实,有混淆阶级斗争之倾向。”他收到此信后,非常气愤,自认为是很真实的,寓意很深的一篇优秀童话。没办法,只有藏之深山。
不过,他对写小说的意愿没有抹去,发誓认真生活,好好做人,为将来写一部感人的好小说,积累素材。
苦闷来时,吴稚农即拉起二胡,并在二胡的共鸣筒上横了一支铅笔,变成了有韵而无畅声的演奏。当激情来时,便吹起了那哀嚎而颤荡的锁呐,在田野上狂奔。他每日凌晨长跑,到了冬日,在凛冽的寒风中奔跑了一番后,遂即跃入刺骨的冷水河里游泳,试图继续消除那顽固难去的业障。他始终认为:“今生大志未酬!”
每天夜里,吴稚农一刻不停地临摹那本《散氏盘》金文,往往都要写到十二点以后,方才倒床睡去。
他的第四个孩子生下后,即被他夫人王氏溺死。他想多养几个孩子,长大后教孩子们武术,以立足这个不公平的社会,作出应对的积极措施。结果,见孩子刚来到这世上即被人为“夭折”,大哭后,与老婆大吵一场。
后来,夫人王氏带了一个最小的女儿,离吴稚农而去。他虽然感到痛苦,但也很同情她,像他这种人,一般女人是受不了的。
在吴稚农关押时,打他、捆他、审讯他的人都认得,路上碰见,他仍与他们言笑,毫无仇恨之相。当人们谈及此人打过你、吊过你时,他说:“没有,如果有,也不是他们故意要打我,那是我自己不好。你们想,石门镇上几千户人家,沈洪浩、王云林、癞痢阿星,为何不去其他人家而往我家里跑呢?那肯定是我晦气当头,或者是我欠了他们的债,那肯定是前世欠下的债,所以千万不能怪打我的人。”
吴稚农的这番话,一下子传遍了整个石门镇。人们评说中,有了两种看法:一种人认为此人已接近愚昧,确实疯了,但疯得可爱。另一种人却认为此人没有疯,那是大智若愚啊!
那些打他搞他的人听后,也是感触良深,毕竟他们也不过是工具而已。
那个癞痢阿星就在那天晚上把手表从窗口还给了人家。后来三个小偷分别判了三四年刑。刑满释放后,都当了搬运工人。除了一个不成家,其余两人都成了家,有了孩子。顺便带一句:癞痢阿星在审讯时,交代了偷手表又归还这一行为,便少判了一年刑。
沈洪浩判了八年刑,在金华蒋堂劳改农场服刑,起先两年内仍是七两米一天,每日唯一的感觉是饿、饿、饿!他写信给吴稚农与瑜荪两个看小说的朋友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饥饿与想吃东西的程度,有一例可以知也。前天在水田里拔草时,边上一人抓到一只泥鳅,便往嘴里送去,那人咬泥鳅时,那泥鳅挣扎着尾巴拍打着他的嘴巴,脸上溅着许多污泥。他用袖子一擦继续嚼着那活生生的泥鳅,慢慢地咽了下去。边上的人只是惊呆,都没有笑。”
吴稚农与叶瑜荪一包一包地把炒米粉寄了去。后来沈洪浩信中写道:“农场里看管机埠的人马上就要刑满释放,我想去顶替,管机埠就自由得多了。我虽然懂电器,但那二十匹以上的电马达我没有接触过。你给我买一本有关电马达的书速速寄来。”书马上寄去。他得着书后,日夜攻读。果然他接替了,总算比田间劳动好上几倍,饥饿感也好多了。
沈洪浩刑满释放后,开了一家电器修理店,修理附近农村机埠的小型电马达,当然是小菜一碟了。他努力赚钱,不到几年,便拉回了以往八年的经济流失,而且超过了一般人的几倍,成了小富翁。接着买了房、结了婚,生了一对双胞胎。
王云林亦不错。他虽然判刑十年,但他一到劳改农场就被领导重视,办了个牙科室,没有受多大的苦,只是每天受着想老婆的煎熬。释放后仍然是做老本行,收了个年轻的女学徒。他老婆虽然没有跟他离婚,但跟别的男人走了。办了离婚手续后,与比他小十多岁的女学徒结了婚,生了孩子。由于他牙科水平高,牙科室办得很像样,也是不到几年即成了镇上的富户。
这种受苦、消业障、得福的过程与现象,按照佛家的观点,是不难找到答案的。
请君留意周围,凡是吃过冤枉官司的或者真的犯了罪,当刑满回来必定还能再创辉煌。尤其是受冤屈的人,更有大的福报。唯有那些犯了罪而隐情不报,或逃之夭夭者,往后的日子定然是不堪设想。正所谓,今世不报,来世必定要报的。
一场视觉革命
1973年初,大队通知吴稚农去公社,那个治保干部说:“吴稚农,为你平反了,你得感谢毛主席。”
吴稚农对那人说:“谢谢,但我不去。告诉你,你去公社里说,你们扣上我帽子,打倒我的时候,我好好的,我根本不是坏人。现在,要为我平反,也就是说你们上次搞错了。嘿,现在啊,我觉得我并不好。随你们便,反正我不去。”
旁边有人说:“毒棺材,你去,可以拿一天误工的。”
吴稚农付置一笑,走了。
石门镇要开拓市河了,把两座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拱型石桥拆除,还有那沿市河建筑的很有水乡特色的水阁商店,拆得荡然无存。吴稚农手头留着的一组全镇照片,这下真的成了唯一的乡土历史资料了。
吴家的两个宅园,全部拆毁,新建房的面积,也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。
三十出头的男子,没有女人是很痛苦的。吴稚农首先想到了凤娟,但又觉得没有面子,或许她的老公管得很紧,所以不能自讨没趣,否则将终生惭愧,因为这种饮食男女之事,本身是要在愉悦的心态下进行,那种尴尬的场合是比没有还要不好,所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后来,桐乡有个朋友,给吴稚农介绍了梧桐丝厂一个老姑娘,二十六岁了,见吴稚农长得英俊,很愿意,在她家过了几个晚上。后来她觉得他身边还有两个孩子,不好,要他把孩子送掉。吴稚农死也不肯,他说:“这一男一女是我的命根子。”结果吹了。后来,一些才貌皆差的女子,人家同意,但他不要。
人们的视觉感受,经历了一场火辣而贫乏的疲倦历程以后,迫切需要有一股温馨而清丽的空气来调节,必然将掀起一场视觉革命。
石门镇上的商店,基本上都属于石门供销社。那个社主任带了吴稚农去杭州的商店参观,由他用照相机拍了一卷胶卷,回来作参考。他说:“可比杭州做得更精彩。”社主任相信,就让他自由发挥了。
这就是有趣的“橱窗装饰热潮”。
吴稚农又在石门镇上大显身手了。虽然这双活比起油漆匠来收入要少一点,但不脏不累又喜欢。他做出了一个模式,但不是千篇一律。比如,在副食品商店里,在烟、酒、糖果、糕点的各个柜子上面,用了七十公分高、两米左右长的三夹板,裱上白纸,用水粉画把这些食品画得像真的一样,而在三分之二的空处留出各种形状,如扇面型、电视屏幕型、圆型、宫扇型等用宣纸画上山水花鸟、兰、竹、梅、菊,就是在文革中要扫除的,又出现了。他在《芥子园画传》中有着取之不尽的源泉,而且画得非常认真,心想,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,把他的拿手墨鸡也搬上去了。每做一爿商店,等于为他办了个小型画展。
在此期间,油漆生意也好起来了,他没有放弃,因为油漆赚钱多,收了几个学徒。
橱窗装饰已扩大到崇福、桐乡、乌镇、屠甸等本县大镇。油漆生意也在向各大镇发展。此时与他的最佳搭挡者,是好朋友叶瑜荪。他们一边做橱窗装饰,一边做油漆,空下来画速写,晚上看小说,摘笔记。白天做活时,便谈小说情节,赞叹小说中的描写技巧。后来叶瑜荪的随笔写得很出色。此后,他专攻竹刻,成为当代竹刻名家,此是后话。
1975年春,丰子恺先生回故里石门,许多慕名者以及一些所谓书画爱好者皆去求画并与其合影。吴稚农非常敬仰丰老,很想去一见,结果他没有去,只是在距离五十米的下塘对岸望了他老人家一眼。
吴顺发对儿子说:“你平日里一提起丰子恺,敬仰得不得了,今日为何不去看他?”
吴稚农回答父亲:“丰老先生已风烛残年,我远远望去,感到他身体很虚弱,正因为我敬仰他,所以我不敢去打扰他,让他平静地看看故乡。再说我一个臭漆匠,去看他又怎么样呢!他不可能把我拉进上海画院。”
张星逸去陪同了,回答了丰老的一些提问。后来吴顺发告诉了张星逸,张星逸说:“你儿子是对的,我是他的学生,去陪同是理所当然,但许多人不知趣,搞得老头子疲惫不堪。”
吴稚农对父亲说:“爸,有好的机会我会抓的,社会肯定在慢慢地变好。你能活过八十岁,你将来一定会看到,吴稚农这个名字,在石门镇上将会排在丰子恺后面。”
吴顺发也只能当儿子是疯子,一笑了之。吴稚农认为,人只要努力求进,必然会有扬眉吐气的时候。这日子在何时到来呢?那是要在一个偶然的机会。他相信莎士比亚的一句话:“幸运是降临给有准备而开始行动的人的。一个努力求进的人,他必须明白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