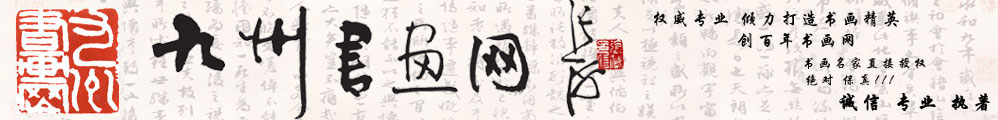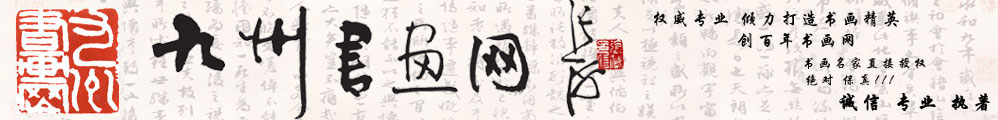“文革”来临
1966年六月,知了的叫声突然低下来,那棵高高的乌柏树发出呼呼的摇晃声,北边推过来一片水灰色的云幕,那路边干燥的土末飞扬起来,变成了一道低低的黄烟,充塞了翠绿的田野。
在田头刚坐下来休息的吴稚农,见尘土中吹过来一张报纸,搁在他腿上,随手翻开,是《浙江日报》,在头版头条上几个黑体大字“揪出三家村黑店(邓拓、吴晗、廖默沙),批判《燕山夜话》”,不觉惊呆了。自言自语道:“我也有这套书。”
“怎么你有这套书?”边上一个年轻人说。
吴稚农又说:“我还有廖默沙的《分阴集》。”
他这么一说,许多人都向他借来看,一下变成了一个风云人物。因为在石门镇只是他有这套书。
不久,石门镇中学成立了“红卫兵”,小学也成立了,接着公社、大队亦都成立了。石门大队很积极,一些贫下中农的青年男女立刻行动。因为需要写标语画漫画,他们就上门去找吴稚农。
吴稚农刚吃过早饭,站在河岸边看对岸寺弄口的横幅标语。他一转身,见几个戴军帽佩红臂章的人,他一见都认得,其中一个东高桥小队的人对吴稚农说:“小龙,你是四类分子子女,只要与家庭划清界线,是可以参加‘红卫兵’的。革命需要你,你快跟我们到大队去,参加革命活动。”这人又补充了一句:“大队有误工补贴,你不要担心。”
吴稚农一想,不对头啊!他们把元帅庙的菩萨砸了,把东圣堂的菩萨也砸了,而且这些都是几百年留传下来的古迹!
“很抱歉,我是富农分子子女,我没有资格当‘红卫兵’。”他连连摇手。
那个人说:“吴稚农,不要不识抬举,我们是看得起你!喏,这是红臂章,你戴。”
“不,不不,我不行。”
“你拿不拿?”那人把红臂章硬塞给他。
“我不能拿。”吴稚农立即把红臂章还给那人。那人不接,红臂章掉在地上。
这下可不得了啦!
“吴稚农,你怎么把“红卫兵”臂章扔在地上。”
“我怎么敢,他不拿牢末。”
那人说:“好,大家看看,明明是吴稚农把红臂章丢在地上。”又指着吴稚农说:“告诉你,你这是有罪的,你污辱无产阶级革命!”
“我怎么敢污辱革命呢?”
“那你跟我们去,你可以赎罪……你去不去?”
那人把红臂章又交给吴稚农说:“你拿不拿?”
“我,我没资格,不能拿。”
“好,我们回去。”那人又指着吴稚农的鼻子说:“你等着吧。”
这五六个戴草绿色军帽、佩红臂章的人气势汹汹地走了。吴稚农看着,呆若木鸡,见他们腰间还系着一只皮带,“这些算兵吗?我不怕。” 吴稚农心里在说。
这下可吓坏了吴顺发。
“你闯祸了?你快去把红臂章拿了吧。”
“我不能拿,干这种事是要遭报应的!”
“报应,报应,你看,报应马上要来了,他们是不肯息的。”
“随他们来吧,反正我又不抢不偷。”
“你呀,比偷比抢还要严重。”
“嘿,你怎么站在他们那边说话?”
“啊哟!我昨天晚上已叫到大队里,给训过话了,要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,不许乱说乱动,要夹着尾巴做人。”
吴顺发又苦口婆心对儿子说:“知道了么,要夹着尾巴做人。”
吴稚农心想,父亲这么一个安分守己、老老实实的人,在解放前,也不跟国民党混,只是一心一意的做生意……现在要夹着尾巴做人。真的想不下去了。他来到园子里,把石担举了几下,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这几天外面的锣鼓声是不断的,然而有一组声音越来越近,终于在吴稚农家门口停住了。接着有十多人的声音同时在喊口号: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。”他们连喊三遍。
当吴稚农跑到堂屋间,那个“红卫兵”头头已在宣布:“我们是奉命前来破四旧、抄富农分子吴顺发的家。”接着他们立刻分头查抄……
方莲珍吓得躲在老屋的院子里,不敢过来。
他们真是翻箱倒柜起来,凡是瓷盘、瓷碗、茶杯、酒壶上面有几个“吉祥如意”或者一句古诗的都被抄走,还有一些木桶漆器上刻有“福”“寿”字样的,甚至连吴稚农母亲的绣花枕套之类的,也一概被抄走。吴家佛龛里的白瓷观音连同佛龛,好在早已藏在夹楼里,故没有遭殃。吴稚农书房里的大批书籍也被抄走,吴稚农很痛心。
“红卫兵”中有一个略有点知识的人说:“吴稚农,你这些书,都是属于封资修的,你不烧毁,还是我们帮你去烧吧……噢,对了,你那套《燕山夜话》怎么不见了?”
“给别人借去看了。”
“限你明天,交到大队。”
因为吴稚农与他有点熟,便与他说了些好话,求他把《芥子园画传》(巢勋本)留下,说道:“这是技法书,是练笔力的,不是封资修。”还有一本《散氏盘》金文,那人翻了翻说:“这是什么书?”
“啊哟,这是象形文字,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,这不必拿去。”吴稚农一本正经地说。
那人总算发了点善心,把《芥子园画传》与《散氏盘》没拿去。
“红卫兵”抬了几箩筐东西,敲着锣鼓走了。
这次使吴稚农最最痛心的是抄走了许多外公的扇面与画轴,一旦烧毁,就永远不存了,那些书倒是暂时的惋惜。他想以后或者国外,肯定会出版的,像秦始皇一样,他要焚烧的书籍不是都传下来了么?
……
第二天,他去朋友家把《燕山夜话》及《分阴集》拿了回来,便速速送去大队。路上他想把《分阴集》扔了,又一想,不好,万一他们查问起来,拿不出来就更麻烦了,他就老老实实地交了。
他在大队办公室外的走廊上,见到一张大字报,头上写着 “最高指示”:
凡是敌人反对的,我们就要拥护。
四类分子孝子贤孙吴稚农污辱“红卫兵”,昨日我们去动员他参加“红卫兵”,他非但不愿意,而且把“红卫兵”臂章隔门槛扔出去。
我们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批判吴稚农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。
石门大队“红卫兵”
吴稚农看后,立刻与他们分辩事实。一个头头说:“你呀,再分辩也没用,群众眼睛是雪亮的,你还是早点回去,等候通知。”
吴稚农轻轻地骂了一声“卑鄙”,掉头就走。
又过了几天,那恐怖的让人心惊肉颤的锣鼓声越敲越近,在吴家停了下来。他们又声称破四旧,搬来梯子,搭在吴家两个落水天井的墙门堂前,用铁鎯头“啪啪啪”地把上面的砖雕人物、花鸟砸坏,还把那砖刻的匾额“居安资深”、“余庆后昆”、“紫气东来”砸掉得一干二净。尽管吴稚农在下面大声地喊:“这是劳动人民用心血刻成的啊!不能砸呀!”
“红卫兵”头头严厉地止住了他的呼喊说:“你们这点算什么呀,你看洪泾桥边的双牌楼石坊,还有南皋桥外的几个石牌坊。雕得好不好?没用!都是封资修,都被拉倒。”
“啊呀,啊呀,你们造孽啊造孽啊!”
“我们造孽?跟我们有什么关系,这是革命!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是风暴,是历史的风暴,你想阻挡,呸!螳臂挡车!”那人振振有词,吴稚农无言以对。
吴稚农想想完啦,这是什么世界?想不下去了。
吴顺发端了一盆水过来说:“红卫兵同志辛苦了,你们洗手……擦手,喝茶。”
吴稚农见父亲如此卑躬屈膝,心想真可笑……算了,别去说他。
又过了几天,锣鼓声又钻心透骨地响过来了,又停在吴家门口了。
这次,“红卫兵”们是掘地破四旧。他们用锄头铁锹在吴家的墙脚、门边、楼梯下等所谓可疑地带挖掘……结果在后楼的楼梯下挖得两甏铜板与一甏银元。他们兴奋极了,又在前楼中楼的楼梯下挖得几甏乾隆、咸丰、光绪等等的铜钱。“红卫兵”们说:“这些是真正的四旧,你们自己肯定不知道,多亏我们帮你们破出来。”
“谢谢,谢谢,红卫兵同志,辛苦,喝茶。”吴顺发一个劲地递茶,给毛巾,陪着笑脸,吴稚农在看父亲的笑脸,觉得比哭还难看。
当“红卫兵”们敲着锣鼓抬着甏走后,吴顺发对儿子说:“这些多是我埋的啊,全是一点一点积下来的,那时是为了防强盗才埋下的。”他吸着烟,叹着气,轻轻地说:“这些人比强盗还厉害。”
儿子说:“你别说了,你积下来干吗呢?”
“我想买地啊!”
“多亏没有买,买多了田地,像外婆家隔壁的徐兆昌,评了地主兼工商,成了真正的剥削地主,那惨了,连这些房子要没收。说了几句不满的话,到内蒙古吃官司去了。”
“那多亏没买。”
“是啊,今天被拿走也不要难过。”
“怎么能不难过呢?我起早落夜,到东阳义乌、到苏北、到安徽。我不抽鸦片不吃喝嫖赌,是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奔出来的呀!”吴顺发说罢,眼泪簌簌滴下。
吴稚农很同情父亲,叫他想开一点,失去了就失去了。如果再难过得伤了身子,又是多了一个“失去”,就当是那时在路上碰到强盗。
一天晚上,将要上楼睡觉时,又传来这不祥的锣鼓声,一下叫人把心拎了起来。果然停在吴家的门口,开始敲门,吴顺发速速奔去把门开了。这次,治保干部民兵队长也过来了,民兵队长说:“吴顺发,叫你老婆方莲珍到大队去交待。”
“交待什么呀?她有病,她神经碰不得。”
“那就让我去吧,反正是坐到天亮,让我多穿件衣服。”吴稚农知道母亲绝对不能去。
“你去没用……你知道你家的金货放在哪里?”民兵队长沉着脸说。
“你们要干吗?这又不是四旧——当然我们也没有了。”
“告诉你,那些金货,虽然不是四旧,但这些是你们从穷苦百姓头上剥削出来的,所以必须上交。”民兵队长对了几个背枪的民兵说:“快把方莲珍叫出来。”
“等等,谁敢去碰我妈!”吴稚农大吼一声。
几个民兵一看不对,马上退后一步,喀嗒、喀嗒立刻枪支上膛。
吴顺发一看要闯大祸了,连忙哀求道:“民兵同志,我儿子跟她娘一样,脑子有毛病,你们不要当真。我去大队好啦,那些金货,我老婆不知道,她脑子有病,托不下的,都是我管的,都是我藏的。”
“好,那就你去。”民兵队长一想,不错,吴顺发就披了一件衣服被民兵带走了。
一到大队,有好多四类分子在毛泽东像前跪着。顺发一见,就主动去跪了。
“吴顺发过来。”有人在喊。
吴顺发立刻过去。
“你先交待,交待得彻底了就马上回家,不彻底的话,你就向毛主席请罪,跪到你彻底交待为止。
“你家怎么只有一对耳环,一只金戒子?你再去向毛主席请罪,去!”一个“红卫兵”在大声叫那个地主婆再去跪。并凶狠地说:“你跪在这两个电灯泡上……跪,快跪!”
只听见“啪、啪、啊唷!”
那人横不住,倒在地上,鲜血从她的膝部染红了她的白裤,慢慢地在水泥地上铺开,她抽泣着不敢大声哭。
“吴顺发,你看见了吗?”
“看见了,看见了,我交待,我是要交待呀!”
“那你说。”并叫一个“红卫兵”记录。
“我家还有四对金耳环,八只金戒子,十根金条,都放在一个罐子里,在后面小院子的月月红花台下部的砖墙里。”吴顺发一溜顺势地说了出来。
“其他地方没有了?”
“没有了,如果有,随你们要我怎么好了。”
“好,我们立即去。”此人马上点拨了三个“红卫兵”,两个背枪的民兵,押着吴顺发来到吴家后院,很快找出了那罐金货。一个“红卫兵”拿出一张表格填好数字,叫吴顺发按上手印就算了事。
“红卫兵”走后,吴稚农起床在后院找到了他的父亲,见他坐在地上无声淌泪,一见儿子便抑着嗓门张大嘴巴说:“我对不起吴家!我对不起祖宗啊!”
“爸,你想开点,这些东西没有用的。”
“你不能跟妈讲,其他都无所谓……”
“好,你肚子饿了吗?吃点东西,睡觉。”
“不饿,我怎么能吃得下东西!”
吴稚农见父亲近五十岁的人了,头发一夜间白了一半多。
1967年春,吴稚农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,是个女孩,取名小蔓。
这年夏收夏种前夕,石门镇上的游街揪斗真是三天两头,戴高帽子的走资派、右派、坏分子、历史反革命、贪污分子、流氓分子、地主、富农等这批所谓牛鬼蛇神。在这小小的一个石门镇上一批接着一批,故此被斗者,只是在被斗时有点难受,因为要跪着爬着在上塘下塘爬过东高桥、南皋桥,大约要一个多小时。如果你人缘好的话,就平平安安的爬过算了,若你人缘不好的话,便得要忍受旁人的脚踢、棒打或是脏东西痰唾等等。当然也有个别人的亲友,在旁边监护,那就好得多。想想被斗的人这么多,看热闹的人也乐此不疲。虽然真的该斗的人也有,然大部分人是不该斗的,所以被斗了后,也不觉得有多大的内疚。
轮到吴稚农的一天终于到来了。因为见得多了,他也并不紧张,小队里的一个“红卫兵”交给他一张批斗通知书,此人还算不错,叮嘱他要穿长袖厚裤,下午二时半到石门茧站报到。吴稚农没有跟父母亲说。
他一到茧站,跨进收茧大厅,马上有人在说:“这是吴稚农,黑帮分子、现行反革命。”立即上来两个“红卫兵”,一个把他的草帽除下扔掉,戴上一个上尖下大的有一只手臂长的高帽子,一面写着黑帮分子,一面写着现行反革命;另一个拿过一块系着麻绳的木牌,套在他的脖子上,他一看写着两排字,上面写着黑帮分子,现行反革命。下面写着吴稚农,三个字上都打了红叉叉。随后,要被批斗的人,陆续到来。批斗时间未到,先命令他们在毛泽东像前跪着。吴稚农转头看了一下,有一个多年在外放蜂的地主儿子张荣昌,跪在他旁边,他认识,便轻轻问“你的蜜蜂呢?”
“都充公了。”
“你现在靠什么呢?”
“在杨家庄小队劳动。”
“日子好过吗?”
“怎么好过呢?我有四个孩子,都还小呢?”说着,潸然泪下。
“不许交头接耳,好好向毛主席请罪。”“红卫兵”的喊话,中断了他们的对话。
三点钟一到,便进行批斗,一共有十多个人。
当轮到批斗时,群众中就要高呼口号:
“打倒黑帮分子吴稚农。”
“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稚农。”
“毛主席万岁。”
接下来是宣读批判文章:
“吴稚农,男,二十七岁,家庭成分富农。此人家中藏有《燕山夜话》,系黑帮分子邓拓的反党黑书,还有廖默沙的《分阴集》。这些黑书,他在石门镇上到处流传,是我们石门地区唯一的一套黑书,流毒甚广,肯定有其黑线串通,有待深入挖掘……
又,此人对革命行动,恨之入骨。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视‘红卫兵’臂章以不屑一顾,掷地弃之。实与他的反革命思想,有着根深蒂固的根源关系。我们必须狠批狠斗。”
读完批斗文,接着又是一阵口号。
……
那放蜂的张荣昌不肯低头,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罪。立刻跳上两个“红卫兵”把他的头,按得很低很低。
当一个个批斗完毕,游街开始了。
走在最前面的是造反派大旗、“红卫兵”大旗,接着是批斗大会的横幅由两个人撑着,紧跟着是锣鼓队。到了南皋桥就命令跪爬,在爬桥前,有一个“红卫兵”拿了一把刷子把墨汁涂在吴稚农的脸上及手上,立刻有人说:“好、好,黑帮分子是应该涂黑。”
吴稚农心想:“这倒好,涂黑了脸,人家认不得我,又看不出我脸上暴露出来的愤恨相。”
爬桥时,向上爬倒还顺当,在往下爬时,便有些吃力,其中一个体力较弱的人,便滚了下去,跌得头破血流,甚是可怜……
要命的锣鼓声敲得正欢,你知道滚下那人的耳朵里听到的是轰鸣声还是爆炸声!
因为没有风,“红卫兵”的大旗像挑着倒挂的一块血布。
这是一个大旱的夏季,天上没有一丝阴云,这天下午四五点钟,正是酷日斜照时分,石板上连一只蚂蚁都看不到。手爬在滚烫的石板上已痛得发麻,身上的汗水顺着双臂淌下,竟意想不到成了一个使手心降温的绝招。吴稚农额头上的汗水和着墨汁淌到下巴尖,一滴一滴洒在他的挂牌上,不知他是故意还是无意。吴稚农这三个字好像笔笔在流淌着黑色的墨泪。
有人在喊:“我口渴,爬不动了。”
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把她手中的半根棒冰送进那人口里,那人流下了眼泪,那个女孩也像要哭了。人之初,性本善啊!吴稚农身体强壮者,不渴也不累,他爬在最前面,爬得较快,他想快点爬完,早点结束这场痛苦的历程,可是后面一些体弱者却觉得有点接不上气。“红卫兵”在喊:“快爬。”
吴稚农一想:“不对,我应该慢点。”就慢下来,有时还停一下……
那些扛大旗的与敲锣鼓的也相应地慢了下来。
爬着爬着,吴稚农想起他的先生郭蔗庭说过:“西藏的佛教徒朝圣,都是跪拜着向前爬行,在膝盖及双臂上留下许多伤疤,那是在消业障,可使今后的生活吉祥如意,充满生机。”他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。“红卫兵”是一个历史产物,但他们的行为太过分,时间长不了。
爬着游街,吴稚农当作消除业障,所以他心里无怨无哀地忍受着,甚至还露出一丝泰然的微笑。
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,吴稚农觉得并不可怕,最难受的是精神上的枯燥,不能画画,不能看书和写字,好在还有一把二胡,就拉《汉宫秋月》,那谱是右派给他的,后来,为避免“红卫兵”的查问,他又拉一些忆苦思甜的歌曲,如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,《汉宫秋月》是很悲凉的,说是回忆苦难是没有疑问的,所以别人也没说什么。吴稚农越拉越有味,只觉得这把二胡太差,发挥不出韵味,就决定去苏州买一把高级二胡。
吴稚农卖掉了家中一些旧铜器,凑了二百元钱,前往苏州。在苏州民族乐器厂花去了七十五元,买了一把一等品二胡,又在新华书店买了《刘天华二胡曲集》、杨荫浏的《怎样拉二胡》,看到此书后附有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,又买了一只手摇留声机,以及刘天华、阿炳和蒋风之等的二胡曲唱片。
这下吴稚农又疯狂地钻进了二胡这块天地,在唱片的辅助下,进步较快,为了寻一地方释放那郁闷的心潮,往往在夜晚,一个人到南皋桥的桥洞下拉奏二胡。那高大的半圆形桥洞,产生了良好的共鸣效果。有时也引来一些真心想听琴的人。藉此,在他的心灵上得着了一些抚慰。
吴稚农不断地抄谱,记谱,渐渐地他学会了作曲。
有时静下来,吴稚农还在想,在美院受辱的事,这一生中要想争回这口气,可能有点难度了。但是不画画也是非常痛苦的事,因为二胡不适合带到田头,那么在田间休息时做什么呢?他讨厌玩扑克,也不想看报。他想,我可以画速写,不画人物可以,因为画人物往往要被指责为丑化工农兵形象。那我可以画牛、画羊、画鸡、画鸭子……
常常有人见到吴稚农在田横地角,跟踪那些东奔西窜的鸡鸭,不停地画速写。一次,他在观看并跟踪鸡时,不小心一脚踏空在地沟里,别歪了脚跟,一拐一拐地走着。别人在背后暗暗地笑,说道:这只毒棺材自讨苦喫。
这下可好了,没人可指责什么了,因为鸡鸭牛羊是人民公社的副业,值得描写。在不断的速写中,真所谓熟能生巧,特别是画鸡,吴稚农抓到了要领,摸着了规律,他从铅笔速写转换到毛笔宣纸的表现,一步步形成了他自己的表现模式,后来成为当代画鸡圣手,这也得“感谢文革”。那是后话。
吴稚农家靠南一个邻居是居民户口的,叫云根,比他大四岁,在镇上清肥所做,每日凌晨四时做两个小时就回家,人们见到他一天到晚在门前河边钓鱼。吴稚农为了得着大量的时间,想去清肥所做倒马桶的工作,云根向所长介绍说:“吴稚农人品靠得住,我和他从小同道,没有偷过东西,去别人家中不会出事。”所长同意了。但吴稚农的父母不同意,认为倒马桶是低下的工作,所以没有去成。这件事,对吴稚农以后珍惜时间颇有警鉴之思。
吴家的家底本来还算不错,俗话说:穷则穷,还有三担铜,但却经不起“红卫兵”三番五次的抄家、搜索,东西所剩无几了。
吴稚农很需要钱,原来可以画肖像,现在的百姓家中只能挂毛泽东像,老祖宗的像是绝对不可能挂的,故此,画肖像也没人需要的。
做农民是又艰苦又没钱,农村里流传着一番谚语:“三世修在机埠上,四世修来泥司匠,五世修来做木匠,七世修来做漆匠。”
吴稚农是个不甘心受苦不甘心缺钱的人。他知道,去机埠管水泵,虽然不受苦,但没钱,而且家庭是贫下中农再通过关系才轮得着去。做泥司匠也很苦,能拿每天三元钱,上交小队一半,还能拿一元五角钱,去做过几天,夏天太阳晒,冬天冷风刮,干不了。木匠在屋里做,太阳冷风都不受,而且工资每天三元六角,吴稚农想改做木匠,但他是个左撇子,在使用工具上带来许多麻烦。他想算了,做油漆匠吧,但油漆匠很少,一般不肯随便带徒弟。
怎么办呢?吴稚农脑子里浮出一句话:“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”
“好,我要做有心人。”吴稚农想起一个在木器社做漆匠的小学同学,便每天去跟他聊天,讲电影故事给他听,偷偷地观察油漆工序,有时候他还帮那同学披披油石膏,打打砂皮,后来那同学知道他要学漆匠,就干脆把技巧教了他,因为在木器社工作是长饭碗,不怕他竞争。
就这样,至多一个星期,他学会了油漆,等于他修了七世的功德。
其实油漆匠很好做,若油漆的家具人家说不够亮,你可再涂上一遍,人家就满意了,而且刷第二遍漆,耗量不大。再说他能画,在橱门上、床上画些风景花鸟,那对他来说,不过是举手之劳,小菜一碟,很方便。当然收入是泥木工的三倍以上,而且别人估计不到。
吴稚农有了这份手艺,人缘也好起来了,那些大队干部、公社干部或者“红卫兵”们家中油漆都叫他。吴稚农肯定给他们便宜,活又做得考究。他那个现行反革命的身份,到后来渐渐地淡化了,也让他更自由了。他得出结论:人生自由无处不在,问题是由你自己争取。为了更自由,吴稚农收了二个学徒。
此间,吴稚农带了学徒们在桐乡县境内辗转做着油漆生活。他们做到哪里,就住宿在哪里。
有一次,他们在一户欲招女婿之家油漆。这一户人家比较节省,早餐给他们吃粥,做到一定时,小便随之急着而来。由于手上有油漆粘着,只得耐着忍一下,可是越忍越急,吴稚农只得擦干净双手,设法解除。本来可以跨过稻地(屋前的白场地)在河边的竹林里方便。可那天下着雨,便奔向那家的坑棚间。他急急地穿过灶间走过楼下房,便到了坑棚间。桐乡农户坑棚间还不小,有猪棚与羊棚,那毛坑插在两棚中间,棚前还有一片空地,置着鸡棚、鸭棚。当他急急地跨进坑棚间,却又放慢了脚步,因为看到一只漂亮的大公鸡在门口洗毛,非常矫健而优美(下雨天,鸡关在家里),为了不去惊动它,可多观察一会,便猫着腰踮着脚走向毛坑……
“啊!姆妈呀——”正巧,那家姑娘在蹬坑,见有人突然过来,便直喊起来。
“啊!对不起。”吴稚农惊慌失措地说,“嘘!你别叫,我没有坏心,不知道你在。我是在观看大公鸡。想把它画出来,怕它变动了位置。”吴稚农又快速摸出速写本子,翻出画鸡的那一页,“你看,我画鸡着了迷。”他摸出铅笔快速在几秒钟内把公鸡画出。
“我吓了一大跳,好了,我知道你人好。”那姑娘边说边拴好裤带匆匆离去。
此件插曲,实非搞笑。吴稚农在做漆匠,没人去逼他画鸡!后来,那种写意画墨鸡,成了“吴蓬一绝”,可以同悲鸿墨马、白石墨虾媲美,看来并非偶然。吴稚农在做油漆时,速写没有停,但二胡很少拉。当时县文宣队有个拉二胡的见到他有一把好二胡,试了试爱不释手,吴稚农就很慷慨地让那人拿去。此人便是后来成为当代水平最高的二胡演奏家傅华根,曾在德国、美国举办演奏会。那是后话。
1968年,全国山河一片红,到处在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、《毛主席与亲密战友林彪》,还有《红太阳》、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江青拍摄的《庐山仙人洞》、《无限风光在险峰》。这就是有名的“红色海洋”与“三忠于”的短暂现象,也弥补了当时民众的精神贫乏,那时各乡各村各户以各种形式在“忠”字上下功夫。
有的在家中墙壁上画上红鸡心,写上三个“忠”字,即“忠于毛主席、忠于共产党、忠于无产队级革命”。号召“献忠字”,掀起了一个高潮。有的在大大小小的圆型的筐、蚕匾上涂上胶水,用食粮五谷粘出三个“忠”字,五颜六色。那些心灵手巧的姑娘们用五彩丝线,用各种材料,绣出三个“忠”字、绣“毛泽东像”、绣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、绣出“红太阳”、绣出“万物生长靠太阳”的字样,还有“雷锋像”、“毛泽东与林彪在一起”的像、“毛主席去安源”等等。还有丝绒剪贴、剪纸,各种灯笼画上样版戏,形式做工讲究的如走马灯一类。当然红心灯、忠字灯是属于最低档的了。小伙子们在汗背心、汗衫上印上“忠”字或者三个“忠”字,那是最时髦不过了。
就是在这一年的初夏,石门地区的民众,除了四类分子外,全体几乎倾巢而出,可谓胜过庙会。从早到夜晚,人们举着尽凭你的智慧做出来的“忠”字,真是千变万化的样式,男女老少背着毛主席语录本,用红布做的袋,袋上绣着“忠”字。手上有提灯笼的、举语录牌的,时而唱着语录歌,时而呼着口号。有高档一点的,拉着二胡或京胡,唱着样版戏。那些可爱的低年级学生们,唱起了《北京有个金太阳》。这些民众走得累了渴了,便坐下来喝自备的茶水,肚子饿了,便拿出面饼糕团、粽子来充饥。一路上唱着、喊着、跳着,有说有笑……
“啊!了不起呀!”吴稚农在家门口看着、感叹着,再想想:“啊,真愚昧呀!”
吴稚农母亲烧了两缸茶在门口施茶,后来得到了好评。
没完没了,走不完的队伍。到了晚上,灯笼点上蜡烛,“忠”字上挂着的小电珠亮了。在扮样板戏的队伍中撑起了汽油灯,一直要闹到午夜方休。人们实在太兴奋、太疲乏了。其中出了一件可笑的事:一个呼口号的领头人实在是疲倦恍惚了,喊起了“打倒走资派,打倒刘少奇,忠于毛主席,打倒走资派,打倒毛主席。”下面的人也跟着喊了。立刻有人觉得不对,马上去揪那人,那人觉得闯祸了,连忙逃到人群中,因为是晚上,看不清要抓的人,一抓抓了个差不多的人,引来好多人把他毒打了一顿,喊口号的人一看被打的人是他的儿子,他立刻过去说明真相,他说我喊错了,我到毛主席像前请罪。据说,此人回到家里被他老婆打了一顿。
第二天,这个喊错口号的人戴了高帽子批斗,大字报一张连一张,结果被评为“现行反革命份子”,与地主富农一起做义务劳动。这种笑话,笑到后来是笑不下去了。许多人评说此事,都说他呼一遍即够了,呼两遍就容易搞错。其实他想深表忠心啊,结果,落得一顶高帽子。冤不冤?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上去毒打,真是不可思议!
1969年春,丰子恺学生张星逸自上海回石门老家,他首先找到吴稚农,两人一见如故。吴稚农知他即是张家厅书屋主人,一问这些书已荡然无存,张先生怪他当初为何不都拿了,犯下这么个大错误。
其实这些书没拿的错误不算大,后来的错误,真是个大错误。
事情是这样的:张星逸回到石门后,潜心研究《诗经》。在十多年时间内,对《诗经》作了详细的注释,写《诗经新话》六篇,并对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进行了新译,准备编《诗经新译》。在此期间,吴稚农帮其誊抄稿子,获得了许多古汉语知识。
关于《诗经新话》与《诗经新译》,张星逸在临终前还未交稿。此时吴稚农正卜居南浔小莲庄。当时张星逸儿子康乐带信告诉吴稚农速回石门,其父欲见一面。当吴稚农赶到石门,见先生已不省人事,其子康乐呼叫不应,当说到吴稚农来看你了,张星逸即刻睁大眼睛,连头也抬了起来,吴稚农抓住他的手说道:“先生有何交待。”老人已不能开口,只用手在空中写划了一下,又摊了摊手,接着略略拔动了几下指头。吴稚农当即领会,是要稚农把他《诗经》稿子拿去。吴稚农的第一反应是不能拿,因为很有价值。第二是他自己有很大的抱负,这些东西虽然很价值,然对他来说,不足为奇。便想到了康乐虽然没多知识,但康乐的两个儿子大毛十岁、二毛八岁,读书成绩很好。遂即说道:“先生你放心吧,张家后继有人,大毛二毛成绩很好,这些稿子留着让他们来接收吧。”吴稚农说完,遂转身关照康乐。张星逸即刻闭上眼睛走了。
几年后,有人见张康乐背了两麻袋稿子在废品收购站出售。有个略懂文物的人知后赶去,只捡了几本《张义仁医案抄本》,因张星逸少年时曾向乌镇的浙北名医张义仁学过医,这些医案皆以毛笔抄写,故此人略为多出些钱把它收进,其他一些稿子皆是圆珠笔抄写或复写纸印件,故不感兴趣。
当吴稚农赶去废品站,说那是几个月前的事,东西早已回炉。
吴稚农顿足不已,扼腕长叹。
其实那是张星逸找错了人,他认为吴稚农人厚道,不可能将书稿占为己有,但他不知吴稚农有一股豪气,竟然对此不足为奇。然而换作那些有心机者,肯定对此重视,此稿定然保留传世。
故此事之教训,留给后人两句话:厚道之人不一定能办妥大事,有心机之人却能承接大事。
张星逸曾经在研究元曲中的俗语词,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吉川幸次朗教授、横浜大学的波多野太郎教授有信札往来。当然像此类文件只有去上海邮寄,才可免去许多麻烦,就托吴稚农往上海投寄。
此时,吴稚农通过做油漆工积累了一些钱,经济尚可。他带了些钱去上海,听张星逸说在上海的旧货寄卖店中,有许多照相机很便宜,可以买回来拍照赚钱。
果然,吴稚农去上海先把信件寄出后,便在南京东路的旧货店中买得一只折合式的德国蔡司照相机,不到百元,也有半成新。经店员介绍,又去了不远的王开照相馆。他在“王开”买了二十卷120胶卷,二号三号印相纸各一盒。又看到橱窗里有几本吴印咸的摄影知识小丛书,他细细翻看后,觉得大有天地,都买了后,又按照书上的印相配方,买了显影定影的药粉。
这次他满满的买了一批东西。回到家中立即做了一只印相片的箱,并在小厢房里布置了一个暗房。在板壁上凿了一个小方洞,可以在白天印相。
此时乡下的各大队,甚至小队的仓库与养蚕的共育室墙壁上都需要画毛主席像,吴稚农此时有个很好的合作伙伴,是经常与他交换看小说的叶瑜荪,他爱好文学,也能画,搞起油漆来也一学就会。加上张星逸当时身体还行,三人在石门附近油漆、画像、拍照,忙得不亦乐乎。
要拍照的人很多,特别是大队文宣队里的男男女女。吴稚农他们白天拍摄,晚上冲印,第三天的上午可以见到照片。这些年轻人见到照片兴奋极了。因为画画的缘故,吴稚农拍的照既快又好,取景构图比一般高出不知多少。比如拍一个人站着,可以叫她站在树边,一回头、一侧身、一露脸、微微一笑,生动自然,而且为她题一名词,如等待、回顾、企盼、期望、怀念、认可、沉思、喜悦等等,画面一下激活了,让人欢喜莫明。
再说那些文宣队的演员,他们化了妆,拿了道具,如“智取威虎山”、“奇袭白虎团”,可在野外的岗屯上,渠道沟里拍摄,照片一出来,活像电影里的场面。他们拍了又拍,印了再添印。吴稚农在印相时偶然产生的失误,如不小心夹进了一小片纸屑或灰尘,或曝光过度或显影过度,给了他很大的技巧启示。比如,有时在大雾天拍摄一些送别、约会,就用剪好的小圆白纸,夹离一块玻璃,印成朦胧的月亮,可使画面诗意盎然。那是附近大镇上的照相馆中从未有过的优秀作品。
在此期间,吴稚农又对家乡石门湾拍摄了好多能显示江南水乡特色的风景照片。因为他的蔡司相机上配有浅黄浅绿的滤色镜,所以效果很佳,连美丽的云彩都能拍得生动如画。
在拍照中,吴稚农曾做了一件好事,一件成人之美的好事。
一次,在一个村上的文宣队里拍照,因为拍了多次,人员都熟了。这天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悄悄地对吴稚农说:“小龙阿哥,我想要你帮个忙,事成以后,我会好好谢你。”
“你说吧,应该帮的,我肯定帮,不用谢,不应该帮的,我绝不会去做。”
“你认得吗?就是那个两条长辫子的小英。”
“我认得。”
“她跟我已好得不得了啦,但她父母不同意,嫌我们家弟兄多。我想与她拍在一起,但又怕她不好意思,是不是能拼在一起。”
“那不能,这样做要给人家骂的。”
“那怎么办呢?”
“行,我有办法,等会我跟她拍的时候,我叫你过去帮她把头巾放放好,你就大大方方地过去,伸手放头巾时,你侧过头来对着镜头微笑一下,懂了吗?”
“懂了,懂了。”
一个接一个地拍着。
当拍到那个叫小英的姑娘时,吴稚农对她的姿势变动了几下都说不好看,说最好拿一块薄纱头巾披一下。当时立刻有人递头巾,她披着后,吴稚农说:“不对,你披高一点……再低一点……不对……”
“嗳,你帮她放一下。”
那小伙,正在边上,立刻过去伸手一碰头巾,一微笑。
“卡嚓”一声,“哎哟、哎哟,我不小心碰了一下。”
“那怎么办啊?”小英发起嗲来。
“没事,不算你钱,重新拍过。”
就这样很轻松地拍完,那小伙递给吴稚农一个纸条,写着:印二十张,钱加倍。
结果印出来一看,自然得不得了,是一张佳作。后来小伙子到处分送,那小英也高兴。村里传开了,小英父母也没有办法。第二年春天,他们结婚了。吴稚农把那张照片放成十二寸,他们配了个镜框挂在新房里。
据说他们生了一男一女,很美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