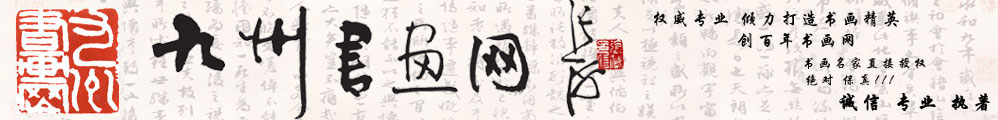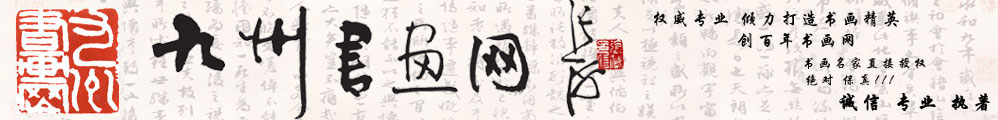图书之缘
吴士龙自桐乡画图归来,正是稻禾飘香时节。公社怕他出外画人像,需要他时又找不到人,便让他在营里(即生产大队)做个统计员,报报生产进度,只须每天到各排(即生产队)里去转一下,可以问一下,也可以不问,就向公社汇报一只表格上的数字,可以凭感觉,差不多上报一下就可以了,关键是必须日日上增,而且每天在指定时间内上报,千万不可怠误。
开头几天内,吴士龙倒很认真地去查问。一次,他来到镇西郊的扎网村,一下子呆住了,原来亩产万斤的试验田在这里。见田头一块木牌,有教室黑板那么大,上面的大字是“万斤试验田”,下面写着一排公社主要领导的名字。再看这些稻禾,长得密密麻麻,有的已闷得发了黄。见那边有几个在用手摇风车扇风灌气,还有几个人在用竹竿挑开稻梗,让风灌入其中,达到通风透气的效果。吴士龙觉得真是不可思议。这是多繁的事呀!一看有十多个人,都是贫下中农,有的还是共产党员,因为这些人是共产党信得过的人,对党最忠诚的人,据说他们已经如此干了十多天,估计还得干一二十天,直到高产出来为止,也就是“卫星上天”。
仔细一观察,他们个个都是汗流浃背,满怀信心。吴士龙见到这些人如此之认真,如此之效忠,他非常感动。对这些人说,我明天再来,要来画速写,画好后要在《桐乡报》上发表。他们高兴极了,都说:“好、好、好,你明天来画。”
第二天上午九时,在那清秋的艳阳下,吴士龙带了画夹匆匆赶到,一见更是奇观一大,他们新增添了几块大镜子,因为昨日是阴天,今日阳光灿烂,大镜子把阳光反射到稻禾的阴面,这是科学!夺高产是离不开科学的。
吴士龙很是激动,便把这些都画了下来,他边画边在想,真了不起,这项夺高产工程,动用了数以千计的劳力。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,如果用在我学画的专攻上,那必定成为大画家。
正画着,有人在说:“能把我们这些人画上吗?”
“能,但是认不得是谁……除非要有明显特征的人。”
“喏,要么把瘌痢阿三画上,他特征最明显了。”其中一人喊了起来。
吴士龙知道阿三是党员,说道:“他戴着草帽是看不出来的。”吴士龙觉得好玩又为难。
“好,好!”有人在叫好,忽见阿三自己把帽子摘了下来。吴士龙觉得画着不成体统,如果不画,又觉得对不起他这个党员,所以没有把他画在主要地方,只是在中间画个光头,头上稀疏的画上几根头发。
阿三看了非常满意,立即摸出香烟递给吴士龙一支。吴士龙不抽烟,说道:“谢谢,我不会抽烟。”
后来此画在《桐乡报》上发表了,题目为《高产田走向万斤》,引起了一时轰动,尽管这块高产田后来只收了几十斤瘪谷。
一次,吴士龙在办公地张家厅的一个楼梯过道边,站在凳子上张贴进度表,当他转身时,在对面一块脱开的板壁中见到了里面房间内有许多书。书!吴士龙对书是大感兴趣的,他受到了诱惑,驱使他走近那扇门,但门是上了锁,他在无奈中拨弄了一下锁,这把生了锈的旧锁忽然脱开了。吴士龙喜出望外,一见无人,便入内大翻其书,果然有许多好书,他挑选了一叠书,拿出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抽斗内,此中有《小说月报》创刊号与第二集,曹聚仁小说、蒋光慈小说、徐志摩《新月集》、丰子恺漫画《学生相》、《人间相》。里面还有好多杂志,如《白鹅》、《红叶》以及好多珂罗版名家画册。他仍把门锁上,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这些书,并摘录了笔记。确实这些书对吴士龙的影响颇大,使他后来步入文学之路起了不可磨灭的开启作用。吴士龙看完后,仍把这些书放入房内,唯独把丰子恺的漫画带到家中,临摹了好几本,舍不得归还。后来大队办公地迁往镇北通市桥边的狐仙堂,张家厅归石门镇政府办公。这些书的主人是后来吴士龙的文学老师张星逸。他与老师谈起这些书,老师说,里面的书已荡然无存,被人拿走了,很可惜。张星逸怪吴士龙太老实,当时为何不都拿走。
自从在桐乡画了一段时间的水彩画后,吴士龙对水彩画的兴味很浓,在家里常常作些水彩静物写生。还有一个偶然的机缘,一位上海亲戚送来一盒糖果,是用一张《文汇报》包着拿来的。吴士龙有一习惯,凡是须扔掉的报纸,总是要用眼睛扫一遍,收视一下是否有值得看的。凡是有那些意有不舍的妙文,都把它剪下来。吴士龙看到报纸上有一篇日本作家夏日漱石的《旅宿》,是丰子恺翻译的。篇中有一句写道:“有时,一个人在山间的小路上,背着画箱,拎着三脚凳,坐下来画着水彩画。”“啊,这是一种多么富有诗意的情景呀!”吴士龙叫了起来,他要效法一下,便热衷于水彩画写生。
吴士龙去西药店买了一只白色卫生箱,把它漆成天蓝色,常常背着去镇东郊的洪济桥、南郊的观音堂畔,还有西竺庵对面的笠影亭,他家对面的寺弄口,其东高桥与南皋桥,他画得最多。尽管他的行为,在小镇上的人们看来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,尽管有些人开始叫他“毒举”或者“毒棺材”“毒头吴士龙”(即疯子或者神经病),然而他却旁若无人,乐在其中。有人当面说他傻,他却振振有词地说:“我喜欢画画,或许能成为大画家,我这无休止的画画,是在学习共产党夺高产的锲而不舍的精神!”别人笑着,摇着头,无言以对。时间一长,人们对他的行径也习惯了,不以为奇了。
由于吴士龙是富农子女,他在大队脱产当统计员,贫下中农们意见颇大。尽管公社里常常要他画表或者宣传画,但是共产党最怕的是贫下中农,他们不敢优宠富农分子的子女,只有叫他回小队务农。
对吴士龙来讲,在田里做活,偶尔做一下是很有味道的,若长期做下去就苦不堪言了。他即外出闯荡江湖,以写生画头像,在嘉兴海宁一带,徘徊在乡间小镇上。
当然,这画头像这碗饭也不好吃,画得像,人们就称许夸奖,画得不像,就要听骂声,不给钱,甚至把画撕掉。这段时间对吴士龙来说,也是尝尽人间冷暖。说来真是一把辛酸泪!他回家时,往往是吃过用过,两手空空,最多是带回来几本新买的书。
吴士龙在外面跑江湖画头像,对祖母及父母亲他们来说,也是胆颤心惊、忧心忡忡。虽然他不做农活不拿工分,而且这段时间内不搞拔白旗了,但是他这种行为是不提倡的。如果所有社员都像他一样外出挣钱,那谁去种田?工人老大哥,人民解放军不是要饿肚子了吗?
他们心想,还是去弄个媳妇给他,让他定定心,生个孩子,一者吴家有了后代;二者可以管管他的脚,让他少走走。吴家托了好儿家亲戚,对来了三四家姑娘,那让盲子合了婚。最后,范氏还是认定灵安那边姓王的一位姑娘。吴士龙心想,命运是无法抗争的,就在那年冬天草草地结了婚。
婚后,他还是不好好务农。大队里要办一个初级班(即小学一年级)便叫他去当教师。吴士龙开始很认真,自学了汉语拼音,像模像样地当起了教师,慢慢地又厌烦了,开始替每一个学生画素描头像,或者全身速写,在画速写时,顾不得去管其他学生如何吵闹或者捣蛋。
一次,几个学生把课桌叠成三层高,爬在上面做戏,不意跌下一个摔断了脚,事情闹大,吴士龙被除职回小队劳动。他能正而八经地做农活吗?
农场斗牛
那时,大队里要接管一个小农场,这个农场是公社下放下来的,有七八个做过教师的右派分子,要贫下中农去帮助他们改造思想。
每个生产队抽调两三个青年前去。当然小队里把吴士龙“这筒宝货”推了出去。其原因有二:一是他常常缺工,特别在农忙期间,早工夜工往往不去,在家看书画画;二是他一出工,许多的年轻人哄着他讲电影故事,他正好借题发挥,解除一下心头的烦闷,讲得非常动听,有声有色,连一些中老年人都喜爱听。如此一来,影响了生产,所以小队领导非常讨厌他,便汇报大队,大队干部即带了民兵队长、治保干部,到吴家门小队召开“批斗懒汉吴士龙。”
一晚上,在小队的晒场,当吴士龙被揪出来批斗时,突然吴士龙家隔壁的吴继荣站起来说:“吴士龙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勤进,晚上我们都在河边乘凉,他一个人在房间里,着高统套鞋,穿着厚裤子,在看书写字。”
“着高统套鞋干吗?”有干部问。
“避蚊子,他不怕热。”这个贫下中农的青年吴继荣又说,“下雨天我们打牌,讲笑话,他钻在书房里画画,做双活休息时,我们抽烟、嗑瓜子,他拿出小本子来画速写。如果今天要把吴士龙当懒汉来批斗的话,那我们这些人是比懒汉还要懒汉了。应该先批斗我们。”说罢,他走到吴士龙边上站着,并指着几个同龄小伙子说:“你们有小龙勤进吗?你们过来!”他们有的过来了,有的被父母拖住了。
大队干部哭笑不得。批斗会就不了了之。
后来,吴士龙就被派往涼山坟小农场。那是1962年的春天,当时有许多人看到他挑了一担书一捆纸去小农场。在小农场,他起得很早,在晒场上摆马步打拳,晚上睡得很晚,不是看书就是写字。盛夏的中午,大家都在午睡,他一个人划了一条小舟子,停在树荫下画水彩画写生。人家说他自讨苦吃,他以为挺有诗意。
吴士龙在涼山坟小农场期间,发生过两件轰动一时的惊险事件。
该小农场的人员,是各个生产队抽调两三人而组合起来的,已结婚的也可以把妻子带上,这样有好多对。但有的生产队只来一个人,另一人用一头牛替代,当然这头牛不可能是一头老实肯耕的好牛。正好有一头没有经过阉割的公牛,毛色发亮、力气大、脾气躁,不听使唤。一次此牛弄断了穿鼻的插肖,逃入涼山坟贴边的一条河里,简直无法捉拿。农场队长发出的奖励条文,说谁能捉住可以休息三天,工分照拿。许多人都不敢尝试,因为那公牛很凶,给它抵上一角,可能要招个半死,所以此人必须是有着强健的体魄与胆量,还要熟悉水性,当然还要有智慧。队长一看无人敢上,如果到晚上不能抓回,就会跑到别处,永远抓不回了,那可是一大损失!队长就盯住吴士龙看,心想此事非他莫能。他知道吴士龙水性好,能潜水,而且气力好,见他每天早晨在练罗汉十八拳与抬脚十二路,还在举石担,小农场的小伙子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。
“吴士龙,你难道不敢?”队长斜着眼说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不敢呢?”
“敢,你就上。”
“三天太少。”
“加一天。”
“五天,我就上。”
“行。”
“不过你们要与我配合,我一旦抓住牛鼻子,你们至少要上来三人帮忙,也就是说,一个各抓一个牛角,另一个拿插肖帮我穿牛鼻。当然,这三人,你得给我选好,窝囊货不要。”
“完全可以。”
一切准备定当,吴士龙赤膊,一条短裤。两岸有好多人过来围观。因为河上有一座四米高的石桥,吴士龙站在桥上,叫他们用竹杆木棍之类打拍水面,把公牛赶到桥门这边。
经过一番打拍后,并加上人群的呐喊声,公牛果然来了。当快近桥门时,吴士龙一个翻身下去,此牛非常灵活,即刻掉头逃开,他在水中睁眼一看,是牛的屁股,顺手抓住牛尾巴很快地爬到了牛的背上,他在牛背上坐了一会,用手把脸上的水珠一掳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那时岸上有好多人在助阵,高喊“小龙加油,小龙加油。”那公牛正抬头向一边惊看,就在这一瞬间,吴士龙像一支离弦的箭,眼明手快伸出长臂纵身扑向牛鼻。牛鼻抓住了!那牛头即刻往下沉去。吴士龙非常沉着,他一手死抓牛鼻,一手抓住牛角,心想牛兄,我与你比一比谁的气屏得长……
大约半分钟后,三个助手来了。他们拿来一根粗绳套住牛头,岸上有人在拉。此时吴士龙与牛头同时露出水面,两助手立刻把牛角抓住,另一助手拿过插肖,很快将牛鼻穿住结上牛绳,终于制服了那条犟牛,岸上围观者一片欢呼。此其一。
其二,就在那年夏种期间,耕牛的用途很大。小农场里的这条犟牛,经过这么一场较量,稍微听话一点。由于正处于少壮力旺时期,耕起田来,步子很快,若是碰到体力较弱者,根本是无法驾驭它,几个来回就得换人。
这天有两个人在替换轮流耕田,由于牛走得很快,水田里的污泥,溅满了他们的上衣,还有脸上,看起来很可笑。
吴士龙虽然也会把犁赶牛,但他是个插秧快手,被队长派去插秧,当他插到头后,稍微伸伸腰休息一会,偶然向耕田的两人看去,不觉哈哈大笑。
“笑啥,有本事你来赶。”
“我来就我来。”吴士龙想,插秧插得有点腰酸,耕耕田直直腰,倒也用得着。
“不过你得一个人连着干,不可二人。”那人因为插秧不快,情愿脏一点去干耕田的活,想逼他一人耕,吓退他。
吴士龙不加思索说:“可以,但我必须拿两份工分。”
“同意,同意,你耕吧。”队长立刻接应说。
吴士龙立即脱下长裤前去接替。
当吴士龙耕了几个来回,这头牛的步子慢了下来,知道遇到高手了,因为一般人,当耕到一头要掉头时,往往慢慢地提着犁把转头,吴士龙一到头,即刻提起犁把,脚步“嗒、嗒、嗒、嗒”很迅速地转过头去,牛连喘气的时间也没有,牛有点疲乏了,渐渐把脚步放慢。
吴士龙倒悠哉悠哉,身上也没有多大的泥巴溅上,很是得意。
正在此时,一个声音喊过来。
“嗨,毒棺材,你慢吞吞干吗?你他妈的拿两人工分。”
原来是那个耕田人,他有点气不过。
“不是我要慢,是这牛自己慢起来,你看我到转头。”正好到头,便“嗒、嗒、嗒、嗒”转了,但牛开始有点不情愿。
“快不快,比你们快多了吧?”
“你牛鞭派啥用场,你不抽,它就慢。”
“好牛不须抽鞭。”吴士龙不理睬他。
队长说话了:“吴士龙你耕得这么慢,只能算一个人的工分。”
吴士龙感到队长说话不算数,说声:“快就快吧。”又骂了句,“操那个皮!”便在牛背上狠狠地一鞭“啪——”
此牛感到受了羞辱,从来没人敢这么狠狠地打它一鞭,便“呼——”地一个转身撬脱了牛轭头,抛掉犁把,向吴士龙直奔过来。吴士龙一看不妙,转身跳上田滩,此牛亦奔上田滩,他马上穿过桑林,往王河泾的大路上向北跑去,心想麻烦了,这牛要跟我算总帐了。透了口气,吴士龙回过身去看看这牛的神色如何。
正是不看尚可,一看真叫人胆颤心寒:双眼发红,牛角在坡上像磨刀一样地擦了几下,四只牛蹄在地上蹬踏了几下,呼着大气,口里淌着白沫,向他直扑过来。吴士龙心中着实害怕,但头脑却很冷静。他在河岸的路上,当牛快冲到时,他纵身一跃,跳下河滩。牛扑了一空,前蹄在路上不意一跪,此牛大怒,一想此人狡猾狡猾的,一定神便转头直奔河滩。
此刻河岸两面又站立了好多人在观看,特别是小农场的一批人,有的拍手在笑,幸灾乐祸;有的在指点他,叫他往那条路线跑。吴士龙边逃边回首观察,心想:“如果真的给这头犟牛撞翻,肯定完蛋了,所以要跟它迂回曲折地兜绕,毕竟牛身庞大而笨拙,我可灵活哩。”
吴士龙上到了高滩,这牛也上来,当牛一上来,吴士龙立刻跳下,这样上上下下,眼看这牛口吐白沫动作慢了起来,不过吴士龙也感到累乏起来,心想总得找个脱身的缺口冲出去,他便回过身来往南面方向奔去。正当他万分焦虑之时,一个声音在喊:“小龙,快逃到我这里来。”
吴士龙一看是放牛的老骆,他牵了一条雌牛在路口等着。
此时,那公牛看见了雌牛,它便在河边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水。吴士龙一下子逃得远远的,又在看公牛是不是还要追来。那时他手中已拿到一把铁耙,如果那畜生还要冲来,可以跟它拼了。
竟意想不到是的,那公牛没有冲来,而是向雌牛发出嗯嗯的求爱声,并慢慢靠拢,嗅了一下雌牛的性器,伸出又长又粗的阳巴子,与那雌牛做起爱来。
这些围观的人一阵阵地哄笑起来,哄笑着叫那些娘们多看看。
一些下流痞子在冲着女人调笑着:“杏仙、菊英、美娥你看粗不粗!适意!适意!”
“格只臭棺材,叫你老婆看呀!”
……
在这艰苦而繁重的劳动中,这群苦难之众,暂时得着一些快慰与欢乐。
两牛交合,吴士龙也见到了,但他没有笑,心想:这下可好,我可解危了。再看到那些围观的人,包括那些右派分子,心想:在我危难之时,竟然会如此高兴,真想上去撩倒几个,以便松松这口恶气。再一想:算了,算了,这些可怜人!是在苦难中得乐啊!不能记恨他们,不能记恨他们!
犟牛抵人的事故,少种了好多田,到收工已是晚上八点多了。那时天气闷热,铁嘴苍蝇与乌蚊叮得你难熬。脚腿上痒痒的,原来是浑泥水里蚂蟥在营钻,还有一种水蛆,叮上一口像火烧一样痛……一个女人在抽泣,有人说,做农民是在地狱里。
这一大民瘼,唯有当时做农民的人,才能体味其病痛之至。
后来,这条公牛被拉到牛市场卖了。
那时的农村,即便是近镇的农村,很少看到电影或者剧团演出。这些天天坑在田里苦干的人们,每天都在谈笑着男女床上快事,乐得仰天合地,以排遣他们贫乏的精神世界。人们渐渐地形成了一种习俗,如果这男人不会偷女人便不是真男子,如果这女人没有野老公,这女人肯定是个拗刁货。夏种结束,夜晚打稻、去搬稻时,往往有撞见野合者,正似古人的桑间濮上。
南湖访师
农忙过后,吴士龙有五天假期,便想去上海。他先到嘉兴,住在南湖东岸的第三医院内一个自族堂叔那里。听说在南湖的烟雨楼有嘉兴地区的知名书画家在那里有书画活动。闻说时,已将傍晚,渡船已停,他迫不及待地游水前往。上岸后,便在展厅观看,此中有吴兴的张苕生、吴迪安,海盐的任小田,桐乡的刘雪樵,海宁的沈红茶、孙味齐,嘉兴的沈茹松、郭蔗庭等。凭他对中国画的审美眼光,审视了一会,认为其他的都一般,唯有郭蔗庭的画最有吸引力,他的花鸟用笔雅健遒劲,色彩古艳,其山水墨色淋漓,一派江南雨色,有北宋米家遗韵。吴士龙决定拜其为师,问询以后,得知此人今日已回家中,在广平桥七号。
吴士龙求师心切,即刻游回对岸,穿上衣服,买了几包烟,两瓶五茄皮,赶往广平桥。见郭蔗庭个子不高,四五十岁。面色黑里透红,略带一些油垢。叫过先生,说明来意,郭蔗庭大喜,遂即对他说:“小吴,不客气了,见酒不喝,颇为难过,烦你到外面熟食店买包猪头肉,有爆鱼也行,我们一起边喝边谈。”
吴士龙速速买到,郭蔗庭已倒好酒,呷了一口说:“缘份,缘份啊,你等会先画几笔给我看看。”
“好。”吴士龙即刻起身铺纸,拿起一支长锋羊毫,凝神思考一会。
“你想画啥?”
“我想画几笔兰竹。”
“喔唷,兰竹可难!兰半世、竹白头哪。我到现在还没多大把握呐。”
吴士龙忽问道:“郭先生,你这里有《芥子园画传》吗?”
“有,你要参考是吗?”
“是的。”
郭蔗庭在书堆里翻出《芥子园画传》说:“好东西啊,你在家就照这个学吗?”那是一套《巢勋本》。
“是的。”吴士龙翻开兰竹谱,遂即画了一兰一竹,淡浓适中,恰到好处。
“真好,真好,勿简单。”郭蔗庭真心夸奖,并说,“士龙,明天上午,我同你一起到烟雨楼,你当着他们这些画家露两手,我知道他们画不到这个程度。
“我看他们画花鸟倒很有水平。”吴士龙觉得先生过奖了,便恭维其他画家一下。
“听我说,要把花鸟画好不难,你只要把兰竹画好,其他迎刃而解。不过你还得努力。”说着,郭蔗庭来到画桌前:“我画几笔给你看看,你的用笔出锋,还未收住……”
“对了,我问你,看你小子生得很结实,你练过拳吧?”
“我在练。”
“你在空中给我出一拳。”
吴士龙拉开马步,“呼”的一拳。
“好,很好,你的拳倒留得住。告诉你,画中出笔,须得像出拳一样,也要留得住。”只见郭蔗庭在宣纸上示范了几下,觉得他的用腕好像有弹力,画好后,这枝笔的笔锋仍然是很挺健,使他大为钦服。
那是一个星疏月朗之夜,他迟迟不想回舍。
接着,郭蔗庭又给吴士龙看了许多印章,说:“士龙,你要成为一个大画家,必须攻金石、书法。你想刻好印,必须写金文、摹汉印,当你有了刻印的刀上功夫后,作画出笔就韧炼了。”
“我明天要去上海看英国现代水彩画展。”
“那好。你去上海必须得去福州路古旧书店,买些印谱。”郭蔗庭呷了口酒说,“士龙,你画画必须刻印。你一旦刻印后,拿起笔来作画就不一样,所谓金石文字之交,你将受用一辈子。”说着郭蔗庭从房间角落里捧出一抽斗印章来,让吴士龙欣赏。
“你看,这方,‘且陶陶乐趣天真’是文徵明儿子文彭刻的。疏白文,典雅浑朴。这方‘晓吟楼’朱文,是赵次闲刻的……喏,这方是‘一名荣光’白文,刻得很深,是胡菊麟刻的,哎!他是你们石门人,高手。”说着郭蔗庭翘了一下拇指。
吴士龙听着、把弄着,一下子入了迷。
第二天去上海,吴士龙直奔黄陂路美术馆,参观了“英国现代水彩画展”,他感到非常震撼,画面的干湿处理,技巧很高,特别是一幅雨中街景,光与色的典雅清新,其妙处是难于言表的,唯有在琴弦上,在小提琴或中提琴上方能表达出来。当即他买了一册《英国现代水彩画集》,走出展览馆大门,他一片茫然,觉得英国人水平不得了,中国人无法超越他们。
吴士龙旋即走向福州路古旧书店,他首先见到的是一大批珂罗版画册,大部分是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清末民初画家的画册,他对嘉兴吴秋农,杭州戴醇士之画册颇感兴趣,因为他们的画温润敦厚,又健朴萧旷,还有王石谷的册页,恽南田的册页。然后他在西面一垛书架上找到了印谱,《二金蝶堂印存》、《金壘山民印存》、《赵时㭎印谱》、《苦铁印存》,他都买了。
回家后他看了自己所画的水彩画,不意痛哭起来,认为他一辈子无法去超越英国人的水平。妻子对他不了解,父母以为他真的疯了。此时他的一个画友说:“中国人就该画中国画,没必要去画西洋画。当然,这一说法是错误的。”
吴士龙决定,水彩画没必要再画下去,停了。
这一年的秋收冬种前夕,吴士龙在周边乡下画肖像挣了一些钱,便又去了上海。他一下火车即奔福州路古旧书店。他在翻观旧书时,忽然听人在交谈。
“工人文化宫个边,今朝有老画家在搞笔会。”
“阿拉倒要去看看。”有几个上海青年在说,“一道去。”
吴士龙一想,上海老画家笔会,不妨去看一下,这倒是个机会,遂即跟在他们后面,出得书店门,一直往西走,没多时就到了。听人说,这里是以前的“百乐门”。
吴士龙跟着上了三楼,见到一些老画家在作画。起先,他不知道这些画家是谁,当看到画完后的落款时才知道是谁。一个叫吴东迈的,据说是吴昌硕的儿子,还有叫王个簃、黄幻吾、吴湖帆、江寒汀、孙雪泥。吴士龙观后,觉得比嘉兴南湖烟雨楼见到的好不了多少。后来他停留在一个写书法的老人前,目不转睛地关注着。见写的是草书,写得不快。旁人在说:“写草书是慢写的。笔头墨水不多,能力透纸背。”吴士龙一下子听进了。有人在说,此人是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。当时,吴士龙全然不知,直到往后,吴士龙在1993年攻克章草时,才忆起了王老夫子的行笔方法。真是不可思议,吴士龙只看了短短的几分钟,竟让他受用了一辈子。
上海归来,路经嘉兴,吴士龙又去看了老师郭蔗庭。
这次吴士龙邀请郭蔗庭到石门家中做客,坐一点三十分的石门班轮船,在到达石门家中时已近傍晚,祖母、母亲都出来埋怨他:“你娘子要生孩子了,糊涂鬼啊!”
须臾,接生婆下楼说:“恭喜你,生了个男孩。”郭蔗庭马上笑呵呵地说:“可能是我送来的,将来必定又是个画家,我家是三代画家。” 此子取名小亭,字香舟,多年后,果然成为当今画坛名家,后来,帮助吴士龙画完《芥子园画谱》的花卉部分。此乃后话。
浙美受辱誓言
吴士龙正想去杭州购买《西泠四家》的印谱,正巧碰上一件事,小农场分配到一张糟水票,可以去杭州拱宸桥酒厂提取糟水。因为农场养着好多猪羊,由几个右派在饲养,那糟水可以当饲料。
吴士龙毛遂自荐带着四个青年,摇了一只五吨头的木船,前往杭州。
船到了杭州,先把糟水放满,把船停靠在拱宸桥南畔的河埠口,大家把溅在身上的糟水点子,简单地揩擦了一下,便带了点钱去游玩西湖了。一共五人,除了他外,其他的人都没到过杭州,但他也是七八年前的事了,糊里糊涂的爬上了公交车,从拱宸桥上车,一站一站的过去,不觉乘到了南山路,一看快要过头了,便匆匆下车。有人马上对吴士龙说:“毒棺材,你看看,美术学院,你应该进去看看。”他一想不错,便跟他们说:“我们晚上各自回船,明天一早开船。”
他们便各自去玩了。真是鬼使神差!怎么又来到这个学校门口?
吴士龙记得,十五岁那年刚进这个校门,就被赶了出来。心想,当时年纪小,现在自己二十多岁了,怕什么?去看看他们是怎样上课的,要画的话,我可以出手来几笔,不会慌。
他便把上衣的兰卡其布中山装抽抽挺,领口的纽扣扣上,把头发用手梳理一下,凑着门口人多时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,果然没人阻拦。
走到左面的一个教室边上,一看窗台很高,望不见里边的情景,便踮起脚伸长脖子,看了又看,还是见不到,正欲跨入过道走进去时,忽然有人抓住了他的后领,他转头一看,是一个四十开外的大汉,面孔上有几点麻子,那人严厉地喝道:“你干啥些?”
“我看看。”吴士龙被他拉得喉头有点气闷,便懊恼地说:“你别拉好吗?我又不是小偷”。
“不是小偷,你想做啥些?出去!”那人一口杭州官话,同时用力一拉,“卜”的一声,领口的纽扣崩掉了。
吴士龙一想,杭州佬,过分了吧!
本当一个转身扫膛腿,把他撂倒,但马上忍住,好汉不吃眼前亏,这是他们的地盘。那人真的不客气,一直把他拉到门口,并用力地推了他一把,口中粗鲁地说:“去!下矛不准来。”又是一句杭州官话。门口有许多人在看他。
吴士龙差一点没有把眼泪掉下来,在心里发誓:“我要征服你们这个学校,你这只麻子,总有一天,我要揍你一顿。”
以后,吴士龙每当路过此地,或步行或坐车,忘不了那时被拖的情景。他总是咬牙重复着说:“我要征服这个学校。”当然,他的所谓征服,是指在艺术水平上、学术上。同时又想起了秋月的话:“你自己办个学校,比他们大。”
出了浙美大门,吴士龙速速赶往西泠印社,买了刻刀与一大包印石,又买了几本《西泠四家》及《汉印汇编》。
回到小农场,吴士龙先是摹写印文,待熟练后,即直接写在印石上凑刀。他刻了磨,磨了又刻,有时在左手的食指上滑刀刻伤,鲜血嗒嗒嘀,用布条扎了又刻。磨磨刻刻弄下的石粉泥浆越来越多,把小农场宿舍门前的石阶上弄得一塌糊涂。小农场里的人见了,背地里说:“这毒榉又在发毒劲了”。有人说:“毒棺材,你私刻图章要吃官司的。”“滚,你懂个屁。”吴士龙又气又好笑,把那人骂走。唯几个右派分子,他们很佩服吴士龙,说他不是一般人,对一些好奇的农民觧说,那是在书画上盖章派用场的。
顺便说一下,小农场里的右派分子一共有七八个人,都是一些中小学教师,他们的家庭成分都不好,在反右斗争时他们大放大鸣,被扣上右派帽子。据说每个学校或单位,有分配几个右派的任务,不够,得凑上。因为人总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。再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右派分子,人缘不是很好。尽管你为人正直,也在劫难逃。在右派分子中有一位是美术教师老徐,与吴士龙很投合,由于他一腿跛着,做起农活来慢得很,右派们往往把任务分着干。当其他人早已做完,吃过晚饭,洗过澡,老徐还在汗流浃背地做着。吴士龙便前去帮他速速做完。若遇到要换宿舍搬床铺,右派们皆自顾自搬,吴士龙知道老徐搬起来吃力,便抽身前去帮他,队长说:“吴士龙,你走出来去帮伊,要扣工分的!”“扣吧,一天全扣光都不要紧!没善心!”
老徐听了便哭丧着脸说:“喔唷!吴士龙,你不能对队长这么说呀,我心跳得厉害。”老徐是个胆小人。
【关于右派老徐】
1977年,摘掉右派帽子后,老徐在乌镇中学教美术。后来在中学里办了个职高美术班,培养出一大批美术教师。
老徐的兄长在上海朵云轩出版社任编辑。一九八七年吴蓬在上海朵云轩的画展是其兄长联系安排的,展出了十七天,引起上海电视台的关注,为吴蓬摄制专题片。
【关于浙美事件之后】
连接浙美事件再交代一下:四十年后,吴蓬的《芥子园画谱技法讲座》在中国教育台播出后,便有一位杭州画友,他是武林画院院长,素知吴蓬的书画功力,在一次杭州会晤时对吴蓬说:“蓬兄,我想为你做成一件事,不知你意下如何?”
“五兄,你说。”
“我想把你在浙美挂一个客座教授职称,对你今后发展有利。”
吴蓬对他笑笑。
“你当我吹牛,我跟浙美的关系很好,许多教授的吹捧文章都是我替他们写的。”五兄很自信:“我一句话便成。”
吴蓬说:“谢谢好意,我不要。”
那人不解,说吴蓬高傲得没有道理。
二00四年吴蓬被当选政协委员,他在浙江省政协主办的《联谊报》上,看到一篇题为《曼德拉的开悟》的文章,文中述说了南非总统曼德拉在早年搞独立运动时,被逮捕判刑,囚禁在罗本岛上服了十八年苦役,受到三个白种人狱警的虐待。他忍受了那种耻辱,磨炼了坚韧不拔的意志。当他刑满释放,回南非经过一番不懈的斗争,南非终于独立了,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总统。在就职之前,他诚恳地邀请了三位虐待过他的白人狱警,经安排在贵宾席上,在就职演说之前,曼德拉走到他们三位席前,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全场一片掌声,三位白人无地自容。
吴蓬读后,颇为感慨。曼德拉的忍耐力,宽博胸怀,以德报怨的气度,深深地感应了吴蓬。他对自己说:“你吴蓬算什么呀,有什么了不起的,你怎么可以去恨这个学校呢?你怎么可以去报复揪你的那位门卫大叔呢?告诉你,你必须感恩于这个学校,你必须得去感谢这个门卫大叔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学校给你带来的无限的激机,没有这位很负责的大叔把你狠狠地一揪,崩掉了那颗钮扣,你能感耻吗?能提起那锲而不舍的精神吗?你在第一天上学时,在孙总理像下面的四个大字“礼义廉耻”,你该知道这个“耻”字作用的巨大了吗?
后来,吴蓬在杭州又碰上那位友人,那人还是在提起那桩客座教授的事。说吴蓬的脑子不知是那条筋搭住了,正想狠狠地臭骂起来,用一种诤友的劝说性的嘲骂。吴蓬立刻笑着说:“等等,等等,五兄你别骂,听我说,我开悟了。”
“你能开悟个什么?”
接着吴蓬便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院门口被赶被揪的两桩事,说了一遍,又把在《联谊报》上读了《曼德拉的开悟》那篇文章称颂了一番,所以他也——开悟了。接着对那朋友说:“五兄,你去帮我打听一下,最好能找到六十年代初的那位门卫大叔。”
“你打算怎样?”
“我要请他吃顿饭,一见面,就深深地一鞠躬,并且要赠画一幅。你说呢?”
“行呐。”五兄站起来,在吴蓬的右肩上狠狠拍了一下,接着说:“那客座教授一事呢?”
“那倒不必,我自另有图谋。”
“蓬兄,你已经办了一个大学校。美院的学生不过是上千而已,你的学校是上万的。”
“五兄,你又要笑话我了。”
“我哪里敢?你在教育台的讲课,据说收视率很高!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告诉我,他们在美国都看到了。说你很有功力,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见到新意。”
“这个不算数。”
“怎么不算数呢?看了你的兰竹,比美院的鲁教授高得多呐。他的兰竹凭良心说没有骨力,不大气,因为他不会画山水。蓬兄,由于你山水画得出色,所以你的兰竹柔中含刚,刚中见糯,直追蒲华、吴镇……嗨,都给你们嘉兴人垄断了。”
“那里,那里,五兄你过誉了。”
【关于门卫大叔】
近年来,吴蓬一直在打听那浙美的门卫大叔。
2009年底,吴蓬认识了一位嘉兴籍画家程宝泓,是同龄人,此人在1962年至1965年间曾在浙江美院就读国画系,后来又在美院附中任校长,吴蓬遂把那时在美院受辱之事述说了一遍,欲问讯门卫大叔之人。
“有这么个人。”程宝泓听后思索了一下说,“此人不是门卫,是食堂的员工。因为你所说的方位是靠近 食堂,那时我们用餐若慢条斯理地迟迟没有吃完,他便要吆喝:好了,食堂要关门了。”
程宝泓又笑着说:“噢,我记起来了,你要看的那个教室是画模特儿的,不允许外人瞧看的。”
吴蓬也笑了起来:“啊呀!我也不知道,怪不得他这么凶。”
“好吧,我回杭州给你去打听一下,若有消息,我立即告之。”
后来程宝泓告之,此人许或不在人世了,若在的话,应该近一百岁了。
言归正传。这年冬天吴士龙回家中住了两天。正巧碰上这么一件事。那是一个冬日拂晓,风不算大,却是寒气逼人。吴顺发照平时之习惯,一早起床即往茶馆。当他一出门,就听见有几个人在河边哭泣,寻声去看,发现河湾处一船翻了,男女老少七八人在河滩瑟瑟地发抖,啼哭不已。吴顺发立即唤他们进屋,并叫醒母亲和妻子。
范氏一见此状,便速去房中取出许多旧衣让他们穿上,并叫媳妇莲珍赶紧烧粥。吴顺发问询了他们,知是江苏省的吴江震泽七都人,是两家人,姓沈,由于灾荒,家中缺粮,便载了一船家具,以换食粮,晚上,他们把船停靠在石门镇下塘的转角上,被一拖轮带翻,总算人员无出意外。
七八个人手捧热粥,感激涕零,多亏及时进屋穿衣,没有冻坏身子。
天一亮,范氏便叫孙子去打捞家具,并叫隔壁众人把船翻正,把舱内的水舀干净。
总算东西损失不多,有几样飘流远处的,也被送回来,好人还是多的。
……
这两家人,换得粮食后即匆匆归去。临别,范氏说:“我们家里旧衣较多,衣服是送给你们的,不必归还。”
过了一个月,震泽七都公社寄来了一张感谢状,被挂在石门大队办公室墙上,因为吴家是富农,没有资格挂,大队觉得挂在富农家里是不成体统的。
范氏他们知道后,并不计较。
【关于七都沈家】
改革开放后,吴江七都一带工业办得很好,沈家的儿子沈福昌已办了一个电缆厂。在2003年间吴蓬画了一批画,挂在南浔(七都离南浔仅七里路)的一家画廊寄售。沈福昌走进这家画廊欲买一幅墨鸡图去送属鸡的客户,此画标价两万元,他与画廊老板正在讨价还价时,正好吴蓬来了,画廊老板遂说,:“画家来了,问画家同意就是。”
他们一交谈,沈福昌说:“吴画家好像是桐乡人?”
“对,我是桐乡石门人。”吴蓬笑着说。
“石门人。你知道下塘吴家门?”
“我就是吴家门的。”
“那吴顺发你知否?”
“那是我父亲。”吴蓬笑了起来。
“总算找到了,我父亲老是提起。”沈福昌咧开嘴巴,说道,“吴先生你等一下。”他从包里摸出手机,拨通了家里电话:“阿爸,我在南浔,想买幅画送人,正好碰见了石门吴顺发的儿子,是个画家,哎,……好,……都买了。阿爸,我听你的。”
就这样,画廊里有大小十多幅吴蓬的画,总共二十二万,吴蓬说:“我们有这段缘份,你就付二十万就可以了。”
“不,必须付二十二万。”沈福昌从包里取出钱来说:“我今天只带了两万元,待我明天再拿二十万来,把画拿走。”
“你今天拿去吧,我相信你。”吴蓬坦率地说:“凑机会,我去七都看你父亲,聊聊当年的情景。那年,我大约二十三四岁,家具是我捞的,船里的水是我与隔壁的两个小伙子舀干净的……时间真快。”
“记得我当时才八九岁,”沈福昌也感叹起来,“那时真苦。”
最后,沈福昌把画全部拿走了,第二天上午二十万元如数送到。吴蓬拿出一些提成给画廊老板。
2003年的二十二万,让吴蓬眼前一亮。后来沈福昌又向吴蓬买了好几十万画,2004年,吴蓬在南浔广惠桥堍买了一幢五百平方的宅院。回顾那次救沉船,施衣粥的事,一过四十年,可说是弹指一挥间啊。
回到1963年那次施救之事,吴士龙可有点不解,范氏对他说:“小龙啊,一个人做了好事,阳德被人家接了去,但阴德却留给了我们。你可知道,阴德比阳德大得多呐……”
“阴德大有什么用?”
“阴德大就是将来福报大。”范氏接着说:“再说,你在帮助别人,施舍别人时,心里要想着,你是在还债。还债,你知道吗?债是应该还的,必须还的,还了后心里就轻松了、舒服了……若以后碰到别人帮你的时候,那你得感恩,要终生不忘,不要以为是别人来还你的债,你得报恩。懂了吗?”
“懂了,娘娘。”吴士龙想,祖母是一个文盲,不看书,能讲出这番充满人生哲理的话。忽然觉得祖母这人高大起来。
吴士龙在小农场的岁月匆匆过去了三年。右派们已回归原单位,小农场改制为独立的生产小队,动员各位带家眷前来定居,若不愿者也可回归原小队。吴士龙选择回归吴家门小队,并与小队里商量,在农闲时他要外出画人像,每天上交一元四毛钱,农忙时立即回队务农,因为小队里的劳动值一天也不过是六、七毛钱。小队同意了。从那时起他把名字改为稚农,他觉得在砚田耕作,自己还是个幼稚的农夫。此次把名字改为吴稚农(桐乡口音中,士龙和稚农同音)。
1965年的一个冬天,范氏不行了,她说就这几天内要走了,吴稚农守了一个晚上,深夜时分,范氏轻轻对他说:“小龙,你恨娘娘吗?”
“娘娘,我做啥要恨你?”吴稚农不理解,说道:“娘娘,你做啥要这么问我?”
“你不恨就好,也许娘娘对不起你,但都是为你好啊……你知道小凤结婚了没有?”
“肯定结了。她这么齐整,哪能不被人要去。”
“可是她不会生孩子!”
“去抱一个好了,现在私生子多呐。”
“你去看她过了?”
“我去干吗?她有老公,我有老婆,没必要去。”
“好啊,小龙你懂事了,娘娘放心了。……”
此时,吴稚农已生有一男一女,便拉了儿女们来到祖母床前,他们很乖,“太太,太太”(方言曾祖母)地叫着,范氏应了一声,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
范氏应该说是善终,那年正好是七十岁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