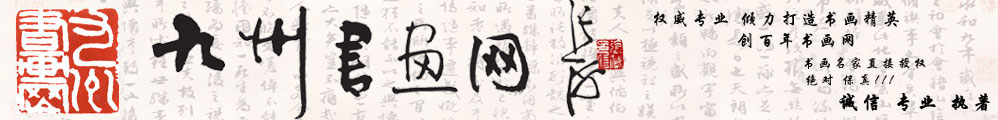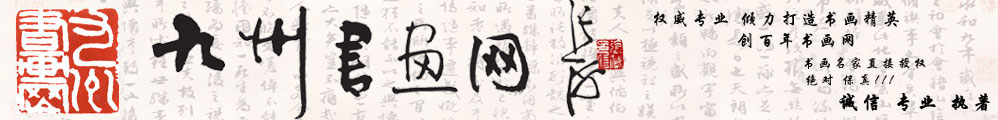【原文】
晋人之书流传曰帖,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,故宋、元、明人之为帖学宜也。夫纸寿不过千年,流及国朝、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,即唐人钩本,已等凤毛矣。故今日所传诸帖,无论何家,无论何帖,大抵宋、明人重钩屡翻之本。名虽羲、献,面目全非,精神尤不待论。譬如子孙曾玄,虽出自某人,而体貌则迥别。国朝之帖学,荟萃于得天、石庵,然已远逊明人,况其他乎!流败既甚,师帖者绝不见工。物极必反,天理固然。道光之后,碑学中兴,盖事势推迁,不能自已也。
乾隆之世,已厌旧学,冬心、板桥,参用隶笔,然失则怪,此欲变而不知变者。汀洲精于八分,以其八分为真书,师仿《吊比干文》,瘦劲独绝。怀宁一老,实丁斯会。既以集篆隶之大成,其隶、楷专法六朝之碑,古茂浑朴,实与汀洲分分、隶之治。而启碑法之门,开山作祖,允推二子。即论书法,视覃溪老人终身欧、虞,褊隘浅弱,何啻天壤邪?吾粤吴荷屋中丞,帖学名家,其书为吾粤冠。然窥其笔法,亦似得自《张黑女碑》,若怀宁则得于《崔敬邕》也。
【译文】
晋人的书翰,流传下来的叫“帖”,其真迹到了明代还有遗存的,所以宋、元、明三代的人研习帖学是适宜的。纸这个东西的寿命至多能保存千年,流传到了本朝(清朝),不仅六朝人遗留下来的墨迹不可能看到,就是唐代人的钩填本,也已是稀罕如凤毛了。所以说,现在所传下来的那些书帖,不管是哪家的,不管是什么帖,大致都是宋、明人的重新钩摹本和多次翻刻本。其名目虽是王羲之、王献之,而面目却完全不是羲、献原来的模样,精神就更不要说了。就好比儿子、孙子、曾孙、玄孙,虽然同出于一个祖上,而身体相貌却迥然相别。本朝的帖学,集中表现于张照、刘墉的书法,但已远不如明代人,更何况其他的人呢!流弊既然这么多,习帖的很难见到有精工的拓本。物极必反,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的。道光朝之后,碑学衰而复兴,因为事势的推移变迁,是不能自止的。
书法发展到了清乾隆时代,对旧有的“帖学”已感厌倦,金农、郑燮,参用隶书笔法来表现,但却失之怪诞,这乃是想求变化而不知如何变化的原因。伊秉绶精通于八分书,他用八分书的笔法来写楷书,师法仿效《吊比干文》,瘦劲绝伦。怀宁的邓石如先生,与伊氏可谓棋逢对手,他除了已经取得集篆隶之大成外,其隶楷又专门师法六朝的碑刻,书法古茂浑朴,实可与伊氏在分、隶上争雄媲美。开启碑体书法的门派,开山作祖的,确当推为他俩。即便以书法论,比起翁方纲的终身专学欧、虞书法,笔墨拘谨薄弱这一点来看,岂止是天壤之别呢?我家乡的吴荣光中丞,帖学的名家,他的书法为广东之冠。但注意观察他的用笔,也像是出自《张黑女碑》的。而邓石如的用笔则是出自《崔敬邕碑》的。
【解读】
由于帖学的衰微不振,清代雍正、乾隆朝而后,碑学的呼声渐起,直至道光、咸丰朝而后大兴。其实原因多多,当与时代文化、时代风尚大相关联,概括而说,实为历史大趋势所致。
康氏言,清代得书法重名者如张照、刘墉,也是“远逊明人”的。此种议论,实嫌武断含混。所谓秦不如三代,汉不如秦代,魏晋南北朝不如汉代,隋、唐不如魏晋南北朝,宋、元、明不如隋、唐,清代不如明代,表面看来似乎符合书法的发展观。诚心而论,书法艺术,一代有一代的风貌特色,是不可以相互替取的。假使将张、刘二人的书法置之于明人间,其精能独到处,想明代人也未必尽能胜之,或更置之于宋、元人,隋、唐人,魏晋南北朝人,两汉人,先秦人、三代人间,想彼辈也一样未必尽能胜之。伊秉绶、邓石如书法自是高古超绝,而郑燮、金农书法也是奇丽多姿,绝不可以用“欲变而不知变者”非之。春兰秋菊,风采各具,康氏以私心好恶妄断高下,不免有扬伊、邓而抑郑、金之嫌。笔者以为有失公允,搞书学研究不可尽信。 |